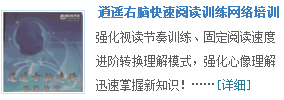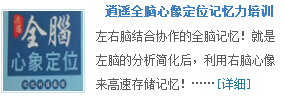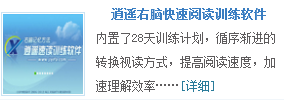《 中国青报 》( 06月19日冰点周刊)
陈平原
编者按
:今高考已结束,有关语文试题尤其是作文的讨论,一如既往成为热门话题。有阅卷老师甚至称,“得作文者得语文,得语文者得高考”。这些热烈的讨论凸显出语文教育的重要性。本报特刊发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的访谈,希望这样的对话能够给目前我国语文教育存在的问题把把脉、开开方。
“知道很多,体会很浅”,这是今天我们文学教育的一个通病
王旭明:最近几我接触了不少北大文学专业毕业的硕士、博士。让我惊讶的是,他们基本上对很多作品都不了解,只会综合各种评论后再自己评论。这么多硕士或博士,无论对于文学研究的某个现象,或社会某个现象,竟没有自己独立的真知灼见。你认为这种现象普遍吗?
陈平原:去我在北大出版社的专著《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在三联书店出版的评论集《假如没有文学史……》都涉及你谈的这个问题。可以这么说,“知道很多,体会很浅”,这是今天我们文学教育的一个通病。我认为,这跟1903开始建立的一整套以“文学史”为中心的教学体系有关。以简明扼要的“文学史教材”为中心,“多快好省”地进行“文学教育”,我开玩笑说,这更像是在学外国文学,只要求学生初步了解某一时代的作家、文类、风格、流派等,并不苛求对作品有深入体会。
今天中国的文学教育,过于强调“系统性”,在我看来,不无偏颇。其实,除了专家,普通人没必要全面掌握丰富的“文学史”知识。一百多来,文学史作为一个知识体系,日渐精微,迅速膨胀。学者们不断发掘新的作家作品,下一代人的文学史图景,必定比上一代人更繁复、更庞杂。这么一来,必须精简书目,有选择地阅读,否则,根本读不过来,也读不好。我再三强调,当老师的,应该允许学生有所“不懂”,且鼓励他们说出自己真正“懂得”的。北大中文系出考卷,基本上不考偏题、怪题,而且可以选答,就是基于此设想。
王旭明:目前高校文学院比比皆是,北大现在还叫中文系,一直没有改名是什么原因?
陈平原:都说要“跟国际接轨”,目前中国大学的“文学院”,绝大部分是原先的中文系“升级换代”成的;而这恰好跟国际主流的大学“不接轨”。香港中文大学的文学院有14个系,包括中文、英文、历史、哲学、艺术、音乐、语言学、人类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等,这倒是跟欧美及日本的大学类似。我们单单是“文史哲”,还不是人家“文学院”的全部,就能分拆成文学院、哲学学院、历史学院、艺术学院、考古文博学院等。为什么这么做?大概是这些大学扩张造成的,鸟枪换炮,“系”改“院”,面子上好看,也便于在学校争资源。另外,“院长”叫起来好听,比“系主任”响亮多了。在公众场合,一般是先介绍院长、副院长,接下来才轮到系主任。好在北大没有强求一律,校长说,你们若不觉得委屈,那依旧当系主任吧。在北大内部,校方将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与其他学院等同视之。北大中文系是百老系,格外珍惜自己的优良传统,不想赶这个时髦。这么顽固地坚守,很多人预言我们兔子尾巴长不了,迟早会更弦易辙的。但也听到不少叫好声。几个月前,我参加一场学术对话,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一见面就说,单凭你们不改文学院,就得敬一杯酒。
“眼学”与“耳学”之间,含英咀华与博览群书之间,找到合适的度
王旭明:能否谈谈你的语文老师和你的中学语文课给你的影响?
陈平原: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上的中学,初中阶段没课上,整天“闹革命”;念高中时,碰上了邓小平“右倾回潮”,总算认真读了两书。我是从插队的山乡跑去念书的,就近入学,进的是广东潮安磷溪中学。教我们语文课的是金老师和魏老师,人都挺好,上课认真,对我很有帮助。但说实话,我的语文修养主要得益于家庭教育。父母都是语文教师,家里藏书比较多,使得我从小养成了读书的习惯。插队8,记得“耕读传家”这一古训,没有一日废弃书本。
这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前不久,我在“纪念77、78级毕业30周论坛”上发现,好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或许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共同特点:缺少正规的基础教育,知识结构上有明显缺陷;好处是善于自学,不墨守成规,无论日后学什么专业,常有超出常轨的思考。还有一点,这代人不管学什么,普遍对语文有好感。因为,在乡下的日子里,语文是可以自学的;甚至可以这么说,语文主要靠自学。
章太炎说过,他的学问主要靠自学,而且,得益于人生忧患。与别的专业不同,一个人的语文能力,与人生阅历密切相关。这也是好多大作家没念过或者没念完大学,以及大学中文系不以培养作家为主要目标的原因。
王旭明:现在的语文课堂或语文老师,是否也应该从你说的这几个方面来培养学生的兴趣呢?
陈平原: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希望找到读书的诀窍,即花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成效。可这一思路,明显不适合语文教学。实际上,学语文没什么捷径可走,首先是有兴趣,然后就是多读书、肯思考、勤写作,这样,语文就一定能学好。《东坡志林》里提到,有人问欧阳修怎么写文章,他说:“无他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做自能见之。”这样的大白话,是经验之谈。欧阳修、苏东坡尚且找不到读书作文的“诀窍”,我当然更是“无可奉告”了。据叶圣陶先生的长子叶至善称,叶老从不给他们讲授写作方法,只要求多读书;书读多了,有感觉,于是落笔为文。文章写多了,自然冷暖自知,写作能力逐渐提升。叶老这思路,跟欧阳修的说法很接近。
现在,不管中考还是高考,考生都会全力以赴认真复习。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恶补别的科目有用,恶补语文没用。因为语文学习,主要靠平日长期积累。记得我参加高考,根本没预备语文,只是复习数学。我想,今天的中学生,大概也是这个样子。不是说语文不重要,而是语文无法突击。语文教学的特点是慢热、恒温,不适合爆炒、猛煎,就像广东人煲汤那样,需要的是时间和耐心。从这个意义上讲,语文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很容易。问题在于,心态要摆正,不能太急。
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有很大差异,不说培养目标,也不说课程设计,就说教学方式吧。以诗文为例,过去主要靠自学,学生面对经典文本,仔细琢磨,百思不得其解,这才去请教;现在则以文学史或文学概论为教学中心,经典文本反而成了“配合演出”。学生省了上下求索的功夫,迅速获得有关作家作品的“精彩结论”。一星期就知道《诗经》是怎么回事;再过一星期,《楚辞》也打发了。一下来,什么李白、杜甫,还有《西厢记》、《红楼梦》,都能说出个一二三。这样的教学,确实推进很快,可学生真的掌握了吗?
晚清西学大潮中,章太炎对那时刚刚传入的使用教科书的标准化教学很不以为然,称:“制之恶者,期人速悟,而不寻其根柢,专重耳学,遗弃眼学,卒令学者所知,不能出于讲义。”以课堂讲授为主,学生必定注重“耳学”,养成“道听途说”的学风。而传统中国的书院教学,依靠师长的个人魅力,以及师生间的对话与交流,自学为主,注重的是“眼学”。在章太炎看来,前者整齐划一,更适合于普及知识;后者因材施教,有可能深入研究。这种对传统书院的理想化表述,有八杭州诂经精舍的独特经历做底,更因章太炎不满于时人对新式学堂的利弊缺乏必要的反省。
当然,现代社会“知识大爆炸”,学生需要修习的科目很多,不可能只讲“四书五经”。不过,章太炎的话提醒我们:贪多求快,压缩饼干式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而且,读书人一旦养成“道听途说”的习惯,很难改过来。如何在含英咀华与博览群书之间,找到合适的度,这值得从事教育的我们认真思考。
大学语文始终没能挺直腰杆,这也就难怪中小学不太重视语文课了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http://www.jiyifa.net/chuzhong/433108.html
相关阅读:余映潮: 积累语言材料的一种妙法
《我的第一本书》课后习题答案
《伤仲永》课后练习答案
《与朱元思书》课后练习答案
《浅议如何构建初中语文教学高效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