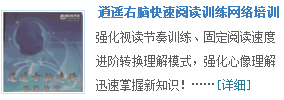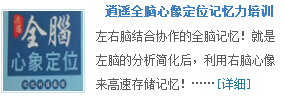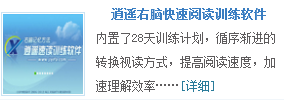篇九象山之学
北宋时,是这种新哲学兴起之时。南宋之世,渐就成熟。
可与朱学对峙的,则象山而已。
朱子说:程门高第,如谢上蔡、游定夫、杨龟山,稍皆入禅学去。必是程先生当初说得高了,他们只瞧见上一截,少下面著实工夫,故流弊至此。
象山学问,实远承明道。
象山: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
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
朱陆之异,象山谓“心即理,”朱子谓“性即理”而已。惟其谓性即理,而心统性情也,故所谓性者,虽纯粹至善;而所谓心者,则已不能离乎气质之累,而不免杂有人欲之私。惟其谓心即理也,故万事皆具于吾心;吾心之外,更无所谓理;理之外,更无所谓事。一切工夫,只在一心之上。二家同异,后来虽枝叶繁多,而溯厥根源,惟此一语而已。(象山之摄万有于一心,自小时已然矣。)
象山之学,极为“简易直截”。
曰:道遍满天下,无些小空阙。四端万善,皆天之所予,不劳人妆点。但是人自有病,与他相隔了。(人的异化,心本善。)
曰:此理充满宇宙。所谓道外无事,事外无道。舍此而别有商量,别有趋向,别有规模,别有行迹,别有行业,别有事功,则与道不相干;则是异端,则是利欲,谓之陷溺,谓之臼窠,说只是邪说,见只是邪见。
(欲做工夫,唯有从事于一心也。)
曰:余于践履,未能纯一。然才自警策,便与天地相似。
对学者言:念虑之不正者,顷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虑之正者,顷刻而失之,即可不正。又谓:我治其大而不治其小,一正则百正。
象山之学,实阳明之学所自出。他俩相似的言语: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劳攘。须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内。当恻隐则恻隐;当羞恶,即羞恶。谁欺得你?谁瞒得你?
象山之学,以先立乎其大者为主。“学者须是打扫田地净洁,然后令他奋发植立。若田地不净洁,则奋发植立不得;亦读书不得。若读书,则是籍寇兵,资盗粮。”
象山与阳明,学皆以心为主,故有心学之称。
朱陆异同,始于淳熙三年的鹅湖之会。朱子之学,所以与陆子异者?在陆子以心为至善,而朱子则谓心杂形气之私,必理乃可谓至善。陆子谓理具于心,朱子谓理在心外。究为一种学问中之两派也。
象山之学,当以慈湖为嫡传。而其流弊,亦自慈湖而起。象山常说颜子克己之学。其所谓克己者,非如常人,谓克去利害忿欲之私也。乃谓于意念起时,将来克去。意念克去,则换吾心体之本然。此心本广大无边,纯粹至善。功力至此,则得其一,万事毕矣。
篇十浙学
理学何学也?谈心说性,初不切于实际,而其徒自视甚高。世之言学问者,苟其所言,与理学家小有出入,则理学家必斥为俗学,与之斤斤争辩。其所争者,不过毫厘之微。而其徒视之,不翅丘山之重。此果何义哉?果其别有所见欤?
理学家曰:言天理而不能用著人事,是谓虚无,是为异学。言人事而不本之于天理,是为粗浅,是为俗学。
职是故,理学家之行事,不求其有近功,而必求其根底上无丝毫破绽。所以贵王贱霸者以此。以一身论,亦必反诸己而无丝毫之嫌,而后可以即安。
理学家之精神,专注于内,事事求其至当不易,故觉得出身任事(做官)之时甚难。自不能不与寻常人大异。寻常人目为迂曲,为背谬,彼正忻然而笑,以世人为未足与议也。(理学家是理想主义,更是空谈者。为了求全责备,不肯以天下为己任。用吕思勉的话说:以天下为己任者,正不容如此之拘。)
吕思勉顺便谈到共产主义。“如谓产当公不当私,岂非正论。然专将目前社会破坏,共产之瞻望,岂遂得达。欲求共产,有时或转不得不扶翼私产矣。世界大同,岂非美事。然欲chai世界于大同”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http://www.jiyifa.net/dushubiji/921194.html
相关阅读:《诸子百家》读书笔记2000字
童年读书笔记摘抄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六册》读书笔记
《慢节奏胜利法》读书笔记
《禅茶,茶中参禅,禅中有茶》读书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