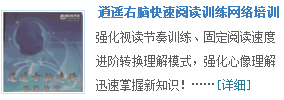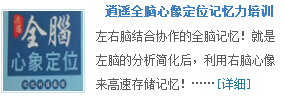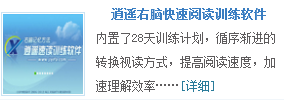量子物理学研究的进展无疑为人类铺就了一条让幻想走向现实的道路。物理学家已成功地发送了光子和原子。目前,他们正对更大的物体和在更过的距离上进行传输研究。那么,何时到人呢?
最美妙的灵感常常产生于缺钱的时候:60年代初,美国电影剧本作家吉纳?罗登贝瑞就因为手头拮据而创造了一个世界性的神话。那时,他计划拍一部给成人看的科幻系列电影,正在寻找一种适当的途径,让定航员在外星球登陆。然而,资金的缺乏不允许他每星期都拍摄一艘宇宙飞船的登陆。
这位聪明的作家找到的解决办法是:在一台魔术装置中,宇航员消失得无影无踪,然后再降落到任何一处希望抵达的地点。他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全部过程,其中,提到一个必须调准的“输送焦距”,并声称,宇航员经由“扫描”和“蜚物质化”,被暂时安置在一个“结构储存器”中:关于输送装置,他只是含糊其辞地称之为“环状锁闭发射器”。就这样,一个令人惊异的“空间置换”的故事被搬上了银幕;在科幻系列电影《星球旅行》中,空间置换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除了平淡地说一句“发射我吧,苏格兰人!”之外,没有人会把它当作话题来谈论。
“发射我吧,苏格兰人”:
对于科幻系列电影《星球旅行》中的探险队来说:“发射”属于日常发生的事情。但对于我们现在的地球人而言,这样一种输送方式还是空想。但是,用光速“输送”人体的最初试验毕竟已经开始。
可是,对于我们这些还未实现这一梦想的地球人来说,这一天才的灵感不仅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也唤起了最美好的幻想:谁不向往自己有一天会被发射出去,或进人太阳,或去休假,或去任何一个地方呢?事实上,许多人已在思考,可否以某种方式轻而易举地完成地点变换。
其中一个人就是美国物理学家劳伦斯?克劳斯。他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我们发射自己去休假之前,还有一大堆“家务活”要先一步完成。克劳斯明确地指出,要把一个人运送出去,还存在着巨大的和几乎不可解决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人的身体是由物质组成的,如果用光速把人的身体移动到另一个地点,那么,就必须将它“唯物质化”。经这位物理学家计算,单单突破原子核内部的限定力,就必须把身体加热到1万亿度──一这比太阳内部的热度还要高几百倍。只有在这一温度下,物质才能变为光,并通过光速输送到任何一个地点。对每一个被输送的人来说,所使用的能量要超过迄今为止人类全部能量消耗的大约1000倍。
第二个问题是:发射仪器必须在目的地将物质重新组合起来。为了知道如何组合,它就需要获得人体所有原子结构的精确信息。据克劳斯估计,每一个原子约为1000字节,诸如原子的位置,原子之间的关系,原子的能量水平,原子的振荡状态等等,描述一个人体的所有原子总共需要1031字节!
这一信息量究竟有多大,可进行一番比较:世界上全部图书所含有的信息为1015字节,仅是完整描述一个人所需要的信息的1亿亿分之一。仅传输这些数据,即使对今天速度最快的计算机来说,也会花去比宇宙年龄还要长2000倍的时间。
前面两个问题,也许通过未来技术的发展可以得到解决,但第三个问题却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精确描述人的原子结构,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能的。理由就是:海森伯测不准原理。根据这一尤其在微观粒子层面上产生效应的原理,我们不可能准确地确定一个粒子的特征。例如,如果我们想知道一个粒子的位置,那么我们就会失去所有关于它的速度的信息,反之亦然。
《星球旅行》的创作者则巧妙地将这一问题蒙混了过去。他们发明了一台使发射成为可能的“海森伯补偿器”。当问到这台补偿器是如何进行工作时,该影片的技术顾问迈克尔?奥库达的回答便是:“好的,谢谢!”
科学家们当然不会如此简单地解决问题。因斯布鲁克大学的蔡林格教授和他的研究小组成功地解决了上述3个问题中最难的第三个问题。他们制造了一个基本粒子的模型,并让它出现在另一个地点。由此可以说,他们发射了人类的第一个粒子!他们的方法是:放弃测定所发射的原粒子的特征──即只发送粒子,而不认识粒子。
为了弄清这一方法是怎样获得成功的,我们必须稍稍深入奇异的微观粒子世界。在这里,最有效的是对我们人类全部健康理智予以嘲弄的量子力学的法则,对此物理学大师尼尔斯?玻尔风趣地说:“谁能思考量子理论而又没被它搞得头晕目眩,谁就没有真正理解量子理论。”
在量子世界中,粒子不只是对我们隐蔽它们的特征,而且还可能同时处于矛盾的状态之中:一个普通的、单色的球要么是红的,要么是绿的;但一个量子球却可能同时是红的和绿的,就像一种50%红和50%绿的混合。只有在我们去观察它的时刻,才会从各种不同可能性的纠缠中产生出一个独一无二的现实:在一部分情况下,它向我们显现为红,在另一部分情况下,向我们显现为绿。人们无法事先说出将会看到什么颜色。
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一个单独的粒子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点。或者说,两个分离的粒子实际上只是同一个粒子。物理学家甚至巧妙地制造出了一种“互逆孪生体”:粒子既分离又相互结合,一个总是另一个的对立面。
就彩色量子球而言,这意味着:两个球在分开的同时,总是着上相反的颜色,这一个是绿的,另一个必然是红的,反之亦然。但只要没有人去观察,两个球就处于颜色纠缠的状态中!只有当物理学家去测定其中一个球的颜色时,才不得不做出选择。而在同一时刻,另一个球也失去了其纠缠状态,获得了相反的颜色──即使它们之间已是光年的距离!这种“幽灵般的超距作用”促使爱因斯坦认为量子力学是错误的。然而,在80年代初,法国的一个研究小组无可置疑地证实这一神秘关联,从那时起,“纠缠的”粒子几乎成为物理学的共有财富。
安东?蔡林格教授(右)和他的同事:在因斯布鲁克大学,他进行的试验是把一个光子的信息从一处输送到另一处。当然,光子与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但如果能把人的信息编成数码,他就可能作为”信息邮件”被“发射”到任何一个地点。
应有如下状态:位于中间的是一个晶体(黄色).它产生出两个相关联的(永久结合)的光子。如果其中一个是红的,另一个必然是绿的。通过测定一个粒子.另一个的状态则被确定──即使相距遥远!对于量子物理学家来说,这种“幽灵般”的超距作用是一种难以解释的现象。
对一个粒子的量子状态的描述包含下述问题:观察者不知道粒子是“红”的还是“绿”的.而粒子也没有决定。
正是这些纠缠的粒子成了因斯布鲁克发射试验中的主角──在此亦可称纪缠的光子。为制造光子,研究才把紫外线光子发射到一个钡晶体上,从而得到了两上分离的红光子,两个“互道孪生体”(专业术语是:“非对称关联粒子”)。如果其中一个发生水平偏振,那么,另一个必然发生垂直偏振,反之亦然。
1993年,IBM的物理学家查尔斯?贝尼特就已清楚地知道,如何用这些纠缠的“互逆孪生体”进行发射试验。他的想法是:如果人们想发射一个原粒子,必须在两个纠缠粒子中选用一个进行试验。这样,原粒子也就失去了它的特征,用来试验的粒子成了原粒子的“互逆孪生体”,而这个纠缠的伙伴则成为原粒子的复制品。由此,人们便发送出一个量子状态,而不去测定它。
经过多年的试验,因斯布鲁克的研究者们将这一想法变成了现实,每小时成功地发射了100个粒子。在制造纠缠粒子的同时,他们还不得不去解决另一个难题:纠缠粒子中的一个如何成为原粒子的互逆的复制品?对此,研究者并未简单地去测定原粒子的特征,因为任何测定都不可避免地要破坏原粒子的特征。
但他们也正是从这一困境中找到了一条出路:原粒子和试验粒子进人一个仪器中,这个仪器可以简单地确定,两个粒子是否以非对称的方式关联着,他们是否是“互逆孪生体”。这种“互逆孪生体”的发生几率为1/4,而它是否发生,不受研究者的任何影响。研究者只是从测量仪中知道,两个粒子处在怎样的关系之中;对相关粒子的各自特征下任何结论都是不可能的。
从总体上看,以下情况发生了:在某一确定状态下,原粒子从左面进入试验装置中,从而失去其原始状态。同时,另一个粒子在右边几米远处突然出现,并在原粒子原有的同一状态下离开仪器:原粒子向右面被发射出去几米远。在这里,被输送的不是物质,而是关于量子状态的信息。贝尼特解释说:“这是一种全新的信息传输方式。”
此外,原粒子在这一过程中失去的原初特征,是不可能事后加以确定的。量子力学的法则严格禁止制造一个粒子的精确复制品,否则研究者就会在这一复制品上测定这一特征,在另一复制品上测定另一特征,从而违反了海森伯的测不准关系。
在因斯布鲁克的研究中,具有原粒子特征的那一粒子曾是另一个光子。但在物理学家看来,情况并不必然如此。法国一个研究小组已经致力于把一个光子的量子特征发射到某一原子上。这样,他们也许可以通过一个原子来研究稍纵即逝的光子的特征。
即使是蔡林格教授,在取得最初的成果后,也在继续从事发射项目的研究。他想把发射的距离扩大:他不仅试图在试验室里,用一根玻璃纤维将粒子发射到几百米以外,而且还试图在维也纳的屋顶上,让一个粒子穿越夜空,射到几公里远的地方。除此之外,研究者们也想在更大一些的对象上试验,例如原子。
对于新型的量子状态传输装置,物理学家希望在量子计算机上获得重要的突破。这是一种未来的计算机,迄今为止,它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仅仅是存在于物理学家头脑里的设想。这种量子计算机不是用单一的数字,而是用“量子位(Qllbit)”计算量子世界所独有的那些奇异的纠缠状态。
由于这一纠缠现象,在我们用一个量子位测定时,立刻就会消失掉,因此到目前为止,从一台量子计算机向另一台量子计算机传送数据,似乎是不可能的。但现在却呈现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不是传送数据,而是将数据发射过去。借助于纠缠粒子,量子状态可顺利地从一台计算机到达另一台计算机。
倘若量子计算机的设想可以实现的话,它所显示出来的功能将是以往无法想像的:例如可能出现运算速度比现在快几百万倍的下棋计算机,人与之对奕毫无胜出的机会。即使秘密警察与巨大的量子计算机比较起来,也只能是自叹弗如:因为它可在几分钟之内破解最安全的密码。但另一方面,即便一台简单的量子计算机也能防止窃听,保证绝对安全的联系。理论物理学家们甚至预言,量子计算机能够计算任何一道物理学的难题。
还是回到“发射”的话题上来吧:如果要采用在光子上成功使用的方法来发射人的话,我们始终都面临着巨大的问题。蔡林格教授承认:“如何将这一方法运用于人,即使在理论上也并不清楚。”但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如果要发射一个人,就必须一下子把他发射出去,而不是一个原子接一个原子地发射。毕竟人体原子的量子状态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不可能将个别原子从其中分离出来。
省钱的发射:《星球旅行》的创作者吉纳?罗登贝瑞为节省资金.想出一种‘发射’的方法使昂贵的登陆成为多余。
穿梭传输:探险队的施玻克先生和如基尔克队长(上图)频繁使用一种物质传送器(远程运输机)。“海森伯补偿器”(左图)可防止故障。
现实并非电影:在电影中.探险队不存在任何发射问题。在现实中则是一个难题:根据海森伯的测不准原理.一个粒子的特征不可能精确地确定。然而,这却是发射结构复杂的人体的前提。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所转移的也仅仅是一种量子状态,并非原物质。任何一个想发射自己的人,都必须首先考虑到,在目的地已经有了一个物质复制品,然后原量子状态才能发射到这一复制品上。如何制作一个人的物质复本,在今天还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在此,我们又遇到了另一个问题:描述人体中的原子,需要巨大的信息量。也许,未来量子计算机可以通过其难以想像的功能帮助我们找到解决的办法。
此外尚不清楚的是,何种纠缠粒子能够同时发送人身上大约1031字节的量子状态信息。唯一可确定的是:即使极小的外在影响也足以摧毁粒子的纠缠,其后果是不可预见的。蔡林格研究小组的同事哈拉尔特?瓦因福尔特坦言:“反正我不会把自己装进我们的仪器。”
而且还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即物质复制品与原物究竟怎样区分开来?我那个原子连原子的精确复制品是本来的那个我吗?他有同样的记忆同样的性格吗?如果我们只是在我们的量子状态中互相区别,那么,是什么把他与我区别开来的呢?
记忆的奥秘(研究者始终未能确定记忆在大脑中的区域)能被置人量子状态中吗?而灵魂又会如何呢?它存在于量于状态中吗?一旦我的量子状态被发射出去,它能获得我的灵魂吗?我原来的身体会出现什么情况,它在物质上完好无损吗?它获得一个新的灵魂了吗?所有这些问题在今天都是无法回答的。只有一点确定无疑:如果发射是以这样的方式运转,那么,在另一端,我原来的身体仍然保留在一个不可想像的状态中。蔡林格解释说:这是“所有由同一物质组成的人的纠缠”。这个纠缠的身体与我本人具有怎样的一种关系,尚不十分清楚,而且纠缠状态所持续的时间也极为短暂。一旦有人对它进行测定(哪怕只是打量一下),纠缠状态就会崩溃,保留下来的是一个完全普通的、单一的状态。究竟是何种状态呢?它与原状态如何区别?
另一个困难在于,在对量子力学的理解上,甚至连物理学家们也不是一致的。涉及到计算,一般不存在任何的分歧。如果是关乎意义,争论便发生了:神秘的纠缠状态会出现怎样的情况?一旦人们进行测定,它真的会选择一种单一的状态吗?或者,在每一次测定时,世界都划分为两个平行的宇宙,以至于从这一宇宙产生这一结果,从另一宇宙产生另一结果吗?或者,只有当一个具有意识的生物去关注纠缠状态时,纠缠状态才变成一种单一的状态?如果这最后一个解释合乎实际,那么,发射人自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的意识很快就会摧毁假定的发射装置。
在蔡林格教授看来,“发射”问题深刻地表明:“我们并没有认清我们在宇宙中的地位。我们扮演的是一个比经典物理学所理解的还更要积极主动的角色。”
在我们真正能够发射人之前,我们还必须回答一些最深奥的宇宙问题。倘若吉纳?罗登贝瑞意识这一点,也许他会更喜欢让他那些星球大战的战士们以完全传统的方式登陆!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http://www.jiyifa.net/gaozhong/1003114.html
相关阅读:萤火虫的尾部为何会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