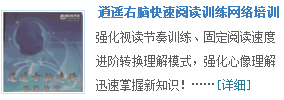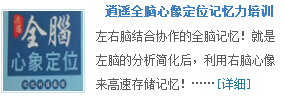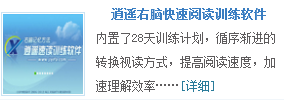(俄)帕乌斯托夫斯基
有时候我也有空闲的日子。于是我一清早就走出家门,步行穿过全城,到诺耶夫花园去,要么就在莫斯科郊区闲逛,多半是普列斯尼亚区和杰维察田野那边。
正是饥荒时期。一天只发给八分之一磅黑面包。我带着这八分之一磅面包,两三个苹果(这是女邻居莉波奇卡供给我的)和随便一本什么书出去,一直到天黑,整天待在外面。
荒凉的郊区包围着巨大的、惊慌不安的首都。有时会传来也是那样遥远的枪声。
……
一个摆渡船的小男孩把我摆渡到(莫斯科河)对岸的诺耶夫花园。那里有高大的菩提树和菩提树的绿荫,因而显得十分庄严。
菩提树正在开花,浓郁的花香仿佛是从遥远的南方的春天带到这里来的。我喜欢想象这个春天,这样的想象增强了我对世界的爱。
诺耶夫花园从很早以来就以栽培花卉而闻名。它逐渐衰败了,荒芜了,到革命前,花园里只剩下了一个不大的温室。但还是有一些上了纪的妇女和一个老花匠在里面干活儿。他们很快和我熟了,甚至开始和我谈起自己的工作来。
花匠抱怨说,如今只有举行葬礼、开隆重的会议才需要花。每次他一讲到这一点,妇女当中有一个——
瘦瘦的、长着一双明亮的浅色眼睛——
好像是为他感到不好意思,于是对我说,很快他们就准会为市里的一些小公园栽培花卉,把花卖给所有公民了。
“
不管您怎么说,”
那个妇女在说服我,尽管我并没反驳她,“
可人没有花是不行的。譬如说吧,无论从前,还是将来,都有在恋爱的人。不用花,怎样才能最好地表达自己的爱情呢?我们这一行是永远也不会消灭的。”
有时花匠给我剪几枝紫罗兰或重瓣的石竹。我不好意思拿着花穿过饥饿和忧心忡忡的莫斯科市区,因此总是用纸很细心地把花包起来,而且包得那样巧妙,让人猜不出我的纸包里包着的是花。
有一次在电车上纸包破了一条缝。我没发觉,直到一个包着白色三角头巾、上了纪的妇女问我:
“
眼下您在哪里弄到了这么可爱的东西?”
“
您要小心点儿拿着,”
女售票员警告我,“
不然,一推您,这些花就全都压坏了。您知道,现在我们的人民是些什么样的人啊。”
“
这是谁在推啊?”
一个腰里系着子弹带的水兵挑衅地问,并且立刻对一个扛着磨刀凳在乘客群中挤过来的磨刀人大发脾气,“
你往哪儿钻?没看到吗?——
这是花。笨蛋!”
……
“
天哪!因为花也要骂人!”
一个抱着吃奶的婴孩的妇女叹了口气,“
我丈夫,别提有多严肃、多庄重了,可是我生这一个,生头一胎的时候,他给我往产科医院里送去了一束稠李。”
有人在我背后焦急不安地呼吸。我回头一看,我背后站着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姑娘,她脸色苍白,穿一件褪了色的粉红色连衫裙,用一双像锡制的、灯碗一样滚圆的灰眼睛恳求地望着我。
“
叔叔,”
她声音嘶哑地、神秘地说,“
给我一枝花!啊,请给我一枝。”
我给了她一枝重瓣的石竹。在乘客们嫉妒和愤怒的谈话声中,小姑娘拼命挤向后门的平台,电车还在行驶时就跳下车去,消失了。
“
完全疯了!”
女售票员说,“
精神不正常的小傻瓜!要是良心允许的话,那么每个人都会要花的。”
我从花束中抽出第二枝石竹,送给了女售票员。上了纪的女售票员满脸通红,都快流出泪来了,她低下熠熠闪亮的眼睛望着那枝花。
立刻有好几只手默默地向我伸了过来。我把一束花全都分送给了别人,突然我在破旧的电车车厢里看到了那么多眼睛里的闪光,那么多亲切的微笑,那么多赞美的神情,好象无论是在这以前,还是以后,我从未遇到过这么多的喜悦和赞美。仿佛耀眼夺目的太阳突然闯进了这肮脏的车厢,给所有这些疲倦而满怀忧虑的人带来了青春。
一个穿着破旧的黑色短上衣、骨瘦如柴、上了纪的人,深深低下头发剪短了的头,打开帆布包,很爱惜地把花放进包里,我好象觉得有一滴眼泪落到了油迹斑斑的帆布包上。
我忍受不了这一切,于是在电车还在行驶时跳下车去。我走着,一直在想,既然这个骨瘦如柴的人忍不住当着大家流泪,那么这枝花想必在这个人的心里引起一些多么痛苦、多么幸福的回忆,他在心中隐藏着自己的老和一颗轻的心的痛苦,想必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节选自帕乌斯托夫斯基《一生的故事》第三部)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http://www.jiyifa.net/gaozhong/343778.html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