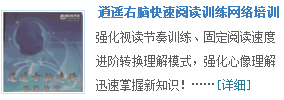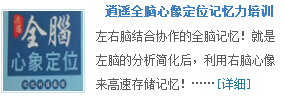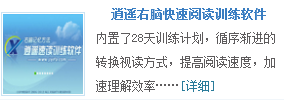王洪勇
①我对纯粹乡村的最后记忆止于2001的那个色彩斑斓的夏天,在张北一个叫马裕村的村庄。
②那种纯粹的乡村影像只有在黑白电影里才能看到,被斜阳覆盖的村中央,有一株历经数百风霜的老柳树,老柳树的躯干虽已斑痕累累,但却仍然枝繁叶茂。一些不知名的鸟儿在老柳树的树干上建造了无数鸟巢。老柳树下有一口古老的砖井,砖井上架着经的辘轳,辘轳左边的青石板上坐着两位轻的女人。女人一边说笑着,一边在飞针走线地纳鞋底,岁稍长的女子用于纳鞋底的针似乎有些钝了,不时的在自己黝黑的发上蹭一蹭。一只老母鸡带着一群小鸡崽在她们周围觅食,老母鸡咕咕地叫着,小鸡崽们的叫声却是柔弱的。老柳树右边有几株向日葵和几株豆角秧在温暖的阳光下茁壮生长,我想这几株向日葵一定不是凡高笔下的向日葵,凡高笔下的向日葵太名贵太有功利性,这几株向日葵在寂寞时光里缓慢生长着,没有人会关心它们的欢乐与忧伤,它们鲜艳的色彩虽然富有诗意,但这种诗意是融入庸常日子的宁静诗意。
③这些影像定格在我的记忆中,在一些无奈的时光里我不由得时常想起。再去张北时,我向当地的一名书法家问起马裕村,书法家笑着说,马裕村早已经在这个地球上消失了!为什么会消失?我瞪大眼睛问。书法家似乎有些责怪我的孤陋寡闻,他说:您不知张北在搞新农村建设吗?现在农民都住进高楼了。书法家在说这句话时还带着一点炫耀。我说那么农民以后就不种地了?书法家说怎么不种地了,地还是要种的,只是农村更城镇化了,现代化了。我说以后农民还养猪养羊养猫养狗养鸡吗?书法家似乎认为我提的问题很笨,竟然很欧式地推开双手说,这个问题只有上帝知道。
④是的,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上帝知道现实中全球化的乡村在渐渐地消失吗?
⑤在乡村渐渐尘封在岁月深处时,我曾在一个雨意缠绵的周末,一个人悄悄地坐上了去青海的火车,到西北歌王王洛宾生活过的地方去寻找歌王的足迹,然而我的寻找显然是徒劳的。7月的青海湖是寂静的,散漫的油菜花在宁静的时光里缓慢盛开,却没有油菜花一样美丽的姑娘在翠绿的草滩上牧羊。时光是寂静的,油菜花是寂静的,青海湖是寂静的,一切都是寂静的,而我却是哀伤的。我知道我不会在这个遥远的地方找到那个美丽迷人的牧羊女,我也知道王洛宾早已成为过去时,但我仍然要去寻找,我要去寻找什么呢?其实我的寻找就是一种和青春有关和故乡有关和诗以及音乐有关,更和梦想有关的乡村情结。
⑥这份乡村情结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农耕民族烙在心灵深处的乡土情结。一个人不管走出多远,漂泊多久,他的内心都装着一方故乡的泥土,即使他故乡的土地贫瘠而荒凉,他也在深深地爱着他的贫穷的故乡,因为这块热土埋藏着他的根脉,润泽和滋养着他的成长。
⑦每一个有乡村生活史的人,心灵深处都会有一方温情和诗意的热土,这方热土就是你精神家园的依托。你乏了累了,它会拥抱你,为你奉送宽厚慈祥的微笑;你潦倒落魄,它会收留你,用温情的双手抚平你心灵的伤口。
⑧可是,在这个浮躁忙乱的世上,哪儿还能找到真正意义上的乡村呢?现实中的乡村即使还保存有一些自然的影像,但往往已失去了生活的韵味,更缺乏精神的底蕴。在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上,同时兼具这些特质的乡村只存留在我们的理想中。
⑨理想中的乡村已经从我们的生活中走远,就像牧歌要从草原上消失一样,我们很难再看到一处用玉米秸秆围起来的农家小院,玉米秸秆上爬满了绿色的豆角秧和牵牛花,粉红色的牵牛花是喇叭状,牵牛花娇艳的喇叭筒里注满了晶莹的露珠,而一位梳着麻花辫子的少妇正站在绿篱笆的一株杨树下,一边纳鞋底,一边和老的女人说话。
⑩让我们苦苦守望的乡村真的在渐渐消失,那些用来饮水的老砖井,那些把女人的容颜都纺老了的木制纺车,那些结构简单的黑白露天电影,那些残存的土墙头,那些银白色的月光下我们所大声歌唱的美好的歌谣。
11 理想中的乡村在远逝的岁月深处,在泛黄的黑白照片里,在我们懵懂的童记忆里。那里有自然天成的美丽景观,那里有最俭朴的原生态生活。那里天空没被污染:大地绿茎如茵,人与动物和谐相处,与自然共生共存,每一株绿草每一片落叶都能找到生存的尊严,每一个人每一个日子都过得散淡而宁静,没有大喜,没有大悲,充满温情,永远安详。
12 然而我们的乡村正在渐渐消失,给我留下的是那些永远鲜活的记忆……
(选自《散文百家》第9期,有删改)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http://www.jiyifa.net/gaozhong/535021.html
相关阅读:《唯物论者启示录》阅读答案
《那山,那桥,那横溪》阅读答案
李敖《红玫瑰》阅读答案
《云和梯田 张抗抗》阅读答案
《雪花落在皇城根儿下》阅读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