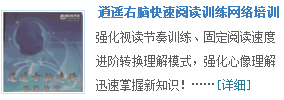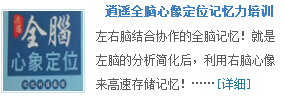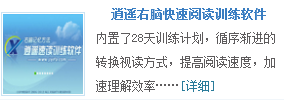他的研究领域集中在那些与人类生活、生命有密切关系的有机物质方面,可以说,他是生物化学的创始人。
不争气的儿子
艾米尔?费舍中学毕业后就被送到姐夫费里德里希的木材厂里,艾米尔的父亲老费舍是德国莱茵地区大名鼎鼎的企业家,他希望这个唯一的儿子能继承他的全部事业。但看来艾米尔绝不是个经商的天才。弗里德里希又跑来告他的状了。
“父亲,我特地绕道来看您,顺便想谈谈艾米尔的情况。”
“他还是那么吊郎当,一点儿没改吗?”老费舍忧虑地问。
“很遗憾,他越来越不像话了,我那里用过的职员不算少,像艾米尔这样的人可没见过。不行,没希望,他什么事也干不成。我派他记帐,他记的帐簿我带来了,当然,这不是正式帐簿,原是让他先练习练习的。要是当真把这件事托付给他,我早就破产啦。这就是那本帐,请您看看吧。”费舍先生把帐簿翻看了几页,只见上面东涂西抹,一塌糊涂。弗里德里希注意看着他的表情。
“请看这儿。”弗里德里希指帐页的一角。
“这是什么呀?”
“化学式子。库房里有一小间空屋子,您能想得到吗?他把它当作化学实验室了。买了一本施托加德的化学教科书,就在哪儿配起什么混合物来了,闹得库房一会儿冒出一股呛鼻子的怪味,一会儿又是嘭地一声爆炸。好几次,他自己从实验室蹦出来,您知道有多狼狈吗?头发烧了,手也烫了……我猜想,他常偷偷摸摸到化学老师那里去,总而言之,我们这位可爱的艾米尔干哪一行都好,就是做生意不行。”
老费舍叹了一口气,听到这些话,他心里很不好受,因为他只有艾米尔这么一个儿子,艾米尔是他全部财产的继承人,最主要的是他的事业的继承人,不错,他还有四个女儿,但其中两个已出嫁,剩下的两个自然很快也要成家的,这一番事业托付给谁呢?老费舍的额头出现了深深的皱纹。
“看来,这孩子是没有经商的才干。只好让他去上学吧!”费舍先生说罢,颓然地坐在椅子上,唉,这个不争气的儿子,但愿他能做个正派人就谢天谢地了…… 生病
父亲做出这个决定是很不容易的,但艾米尔却非常高兴,他马上打点了行装,告别姐夫,回到了埃斯基恒。这时候天气正逐渐变暖,早春的花次第开放,但乍暖还寒的时候也正是感冒流行的时候。艾米尔没能逃脱过去,他患了重感冒。可恶的重感冒又勾起了胃病。艾米尔食欲不振,日见消?,看来去上学的愿望一时半会实现不了。
医生为他规定了专门的饮食,母亲无微不至在照料他,父亲则陪着他长时间地散步,还常常一起出去打野兔、野鸡,这一切都无济于事,艾米尔的病情丝毫不见起色,老费舍只好决定,把儿子送到温泉地埃姆斯去疗养。
尽管如此,艾米尔仍受着沉重的胃病折磨。温泉虽然有助于他病情的好转,但他更需要经常有医生照顾。于是他又被送到在科隆行医的伯父家里,伯母玛蒂尔达热心地护理他,伯父则亲自给他开出病号饭。这种疗法虽很简易,但很有效,艾米尔的病情逐渐好转,终于完全康复,可以上大学就读了。 失望
1871年初,艾米尔动身去波恩,他原是在那里中学毕业的,当年的房东待他十分亲热,使他觉得像在家中一样。
对艾米尔来说,功课并不特别困难,但彼恩大学却使他很失望。在春季到夏季这个学期里,他只能听听课,在学年中间根本不可能得到实验室的位置,只有到了秋天才开始有实验课。
物理和植物学都是艾米尔所喜欢的,但教授们枯燥无味的讲演和使他提不起兴趣,校内对艾米尔?弗舍唯一有吸引力的人物是奥古斯特?凯库勒教授。他是一位优秀的演说家,天才的理论家,卓越的实验家,而且还深受学生的爱戴。费舍也很崇拜他。但是,要想进入凯库勒的实验室,先得经过分析化学实验室。所以,费舍焦急地等待着秋季学期的到来,以便开始分析化学实验。
然而,真等到了这一天,却又使他大为失望。主持分析化学实验的是一位刻板的老教授,他也会采用一些离奇的工作方式,但却只能使学生们感到更头痛。
第一天,费舍从助教那里领到了一只盛着深绿色溶液的烧瓶。
“按规定,分析结果应该在一周内做出,因为您是初次做,给您两周时间。”助教说。
“可是,我根本还不知道分析该怎样做呀!”费舍困窘地看着助教。
“您那里不是有实验指南和图表吗?看一看,自己去干吧!”
费舍犯难地看着他的同学们。这些实习生们偷偷地溜出了实验室,带着发给他们的溶液,然后又不知从哪儿把分析结果带回来交给了助教。
费舍决定自己动手,认真地完成实验分析,而不是像他的同学那样投机取巧。他工作了两周,深钻细抠,按着实验指南?一作了测定。可是,当他把分析结果报告给那位助教时,助教却用诧异的眼光看着他。
“这纯粹是虚构的结果!您的溶液里什么也没有!您怎么会发现镍呢?这镉又从何而来?怎么还有钾呢?费舍先生,重新分析一遍吧!做实验时要细心才好!”
费舍的脸红了,太阳穴砰砰地跳,他感到自己受了戏弄。
第二年,费舍开始做定量分析方面的实验。这时,他对化学彻底绝望了,因为所有的分析都是采用简陋的、早已过时的方法。
“放弃化学,改学物理吧。”费舍打定主意了。 转学
“傻瓜”,费舍的堂兄恩斯特劝他说,“你既然选了化学,那就应该坚持学下去,如果你不喜欢这儿,转学好了。”
“如果到处都是这样的方法搞研究,我是无法干下去的……”费舍的话音还没落,就响起了晃晃的敲门声,走进来的是他另一位堂兄奥托?费舍。
“奥托?!是你呀!你到波恩来干什么?”艾米尔?费舍没有向奥托问好,却先问起他来。
“我想来逛逛呀。我可不能老是守着一个地方不动。总是分析来分析去的……分析得真叫人腻烦。”奥托在大学里学习化学。
“别提了!”艾米尔把手一挥,“我呢,氢氧化铝一过滤就是八天,守着个漏斗,眼睛盯着,滴打滴打地没完没了,谁有这份耐性!我真想把那个架子连同该死的漏斗一古脑儿扔到外面去!”
奥托感到很奇怪:“你们过滤怎么不用本生发明的水泵呢?柏林大学早就用上了。”
“这里连想都没想过。我们这儿全是老一套。”
“我跟你说,”恩斯特插话说,“你转学吧。”
“好主意!”奥托喊道:“我和你一道去怎么样?柏林是个好地方,不过世界之大,何处不可以读书,要出去见见世面。”
艾米尔喜形于色:“就这么定了!去哪里呢?”
“我主张去维也纳,”奥托说,“我听人家说过,那儿有趣的东西可真不少。”
“奥托,可惜那儿离埃斯基恒太远,你知道,我有胃病,离家总得近些才好,你看斯特拉斯堡怎么样?”
奥托沉思了片刻,说:“好吧,就到斯特拉斯堡去吧”。 小有成就
1872年秋天,艾米尔和奥托进入斯特拉斯堡大学读书。他们租了一套两个人住的房间,一起开始学习化学。第二年,恩斯特也来了。
斯特拉斯堡的一切都不同寻常,连人也有点和普通人不一样,据说,由于这个城市长期处于与法国接壤的边境时带,因此,当地居民吸取了法国的许多风俗习惯。
师生之间的关系也不同于一般,费舍弟兄对医学和微生物学都感兴趣,但是,在教师中最吸引他们的却是化学教授阿道夫?冯?拜尔。
拜尔对待这些年轻人十分热情。不久,他就邀请他们到自己家中来作客,教授家中舒适宁静,这里的一切都使人感到适于进行友好而倾心的谈话。
过了一段时间,艾米尔在拜尔教授指导下,着手撰写关于荧光素合成问题的博士论文。这时,对他来说,化学已不再是枯燥无味的学科了。在拜尔教授指导下,工作充满生气,又饶有兴趣,拜尔反复告诫他的学生们一条科研工作的基本原则:“大自然创造出许许多多活的有机体,而这些有机体又是由于百种物质构成的。要了解这些物质,首先要研究它们,然后还要把它们合成出来!只有把它们成功地合成出来,一个科学家才能说是把这项研究工作有头有尾地完成了。”
荧光素合成工作进展很顺利。与此同时,艾米尔还想进行另一项合成实验。他决定先征求拜尔教授的意见。
“我对一种重氮盐,比如氯化重氮苯的还原反应很感兴趣,它的最终产物会不会是肼的衍生物呢?”
“您去试试吧。”拜尔表示赞同。“还原反应曾经导致许多发现。你可以先用锌和醋酸试试看。”
艾米尔着迷似的投入到他的工作中了。“锌和醋酸”,说起来容易,但是,必须选定相应的反应条件,确定反应得以进行的溶液浓度。同学们发现艾米尔一连几天没出实验室,跑过去看他。
“成功了!”艾米尔睁着布满血丝的眼睛大声说,“苯肼合成出来了!”这是费舍对碳水化合物化学的卓越贡献之一,合成了苯肼,并发现了这种物质的实际应用。
胖费舍的建议
一天,艾米尔和奥托去拜访拜尔教授了,恩斯特来了。他和大家打过招呼,问道:“胖费舍到哪儿去了?”
“上拜尔教授那里去了,请你等一会见,他马上就回来。”
因为艾米尔长得胖乎乎的,奥托则相对“苗条”一些,同学们甚至连教授在内,为了区别艾米尔?费舍和奥托?费舍两兄弟,都管艾米尔叫“胖费舍”,实验室的同伴们则干脆叫他“迪克”,迪克是德语Dike,意为“胖子”。
恩斯特在艾米尔工作台前等了一会儿,胖费舍很快回来了。
“艾米尔,我想找你谈谈,或许你能帮我出个主意。”
“你说的是真话吗?你已经是助教,大名远扬的外科大夫啦,我还是个学生,能给你出什么主意呢?”
“你能的,因为问题和化学有关。”
艾米尔穿上大衣,两人就走出去了。
“你知道,我正在研究解剖切片标本,”恩斯特说道,“但遗憾的是,能使组织着色的染料极少,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种新的染料?你和奥托可都是在研究合成染料啊!”
“染料很多,但是,比曙红更好的东西恐怕难以找到了。我亲自做过试验,你看。”艾米尔伸出手指,“这上面染了的色至今还没褪呢。我在合成荧光素时少不了跟曙红打交道,但愿这种染料能使你满意”。
艾米尔的建议的确很宝贵。不久,曙红就成为医学实验室研究解剖切片标本的主要染料之一,从此,应用曙红进行解剖研究,就永远跟恩斯特?费舍的名字分不开了,可是谁能料到,这方面的主要功绩是属于这个化学系学生胖费舍呢? 假期里的旅行
不久,拜尔教授接到慕尼黑的邀请,请他去担任化学教授,在此之前,艾米尔的博士论文材料已准备就绪,他加紧写完它,因为他想在斯特拉斯堡进行论文答辩,这时候他已经决定跟着拜尔教授到慕尼黑去。
这个主意得到了他的堂兄奥托的赞成,可是暑假就要到了,奥托提出一个问题: “夏天我们干什么呢?”
“到维也纳去,你看怎么样?我早就盼着去看看那座名城。顺便还可以了解一下那儿大学的情况,见识见识那儿的实验室。”
在维也纳他们玩得非常愉快,他们在这里结识了许多新朋友,跟他们俩交往特别密切的有化学系学生兹登科?施克劳普。这是一位后来也成了化学家的人。他带领他们游览了这座别具一格的美丽城市。
艾米尔爱好艺术,弟兄俩常去维也纳著名的绘画陈列馆参观。维也纳是音乐之都,他们也从不放过看歌剧的机会。当然,朋友们的手头并不宽裕,他们也没带足够的钱,所以大家经常不得不想方设法找省钱的窍门。
假期要过去了,兄弟俩该回埃斯基恒了。他们回家后又休息了几个星期。但是,他们去慕尼黑的打算遭到了亲人们的反对。因为当时传来的消息,慕尼黑正流行伤寒病。
“你从小就身体不好,不应该去冒这个险,”父亲劝说道。
“但是我要在拜尔教授指导下继续研究苯肼,而这只有在慕尼黑的实验室才能办到。再说,”艾米尔捋起袖子说,“我已经够强壮了,不会碍事的。”
这位早已放弃让儿子经商的父亲说不服儿子,只好让步了。“你已经长大成人,该怎么办能自己做主了。我已经尽到了做父亲的义务,替你在银行存下了一笔款子,数目同给你姐姐们陪嫁的一样多,你随意支取吧。”
“谢谢,父亲,您知道,这对我来说是个很麻烦的问题,钱还是搁在您这儿吧。我想光利息就够我用的了,在慕尼黑,我只会呆在实验室里,而实验室的所需费用并不多,我想告诉您,苯肼的合成,是非常重要的发现,我们还会取得有意义的成就的。”
“对于化学我一窍不通。”老费舍说,“所以,我也想象不出这个发现将会有什么好处。不过,既然你认为它那么重要,你就干吧!” “魔术家”
慕尼黑的工作条件很优越。起初,在有机化学实验室工作的只有费舍兄弟二人,但不久又来了一批实习人员。其中有一个叫库尔蒂乌斯的,艾米尔跟他很要好。
“我真纳闷,您在分析您自己合成的化合物时,怎么要花那么多时间?”艾米尔奇怪地问。
“这还算多吗?”库尔蒂马斯答道。“仅是元素分析就得两天。”
费舍摇摇头说:“真是不可原谅的浪费。”
库尔蒂马斯笑道:“那么您呢?看来您是不会浪费太多时间的。”
“我一天至少做五项分析。”
“一天做五项分析?!这不可能!”库尔蒂马斯吃惊地望着艾米尔,以为他是在开玩笑。
“当然可能,”费舍争辩道,“关键在于把工作统筹好。”
“统筹得再好也不可能。”库尔蒂马斯斩钉截铁地断言。
“不用争论,咱们可以试一试。您就会相信我说的是对的,我是把进行分析的一切工作都事先准备好。”
第二天清早,他们来到实验室,艾米尔点着加热炉,把小瓷坩埚里早已备好的有机物逐一过称,然后动手试验。一张桌子上有两个炉子分别测定碳和氢,另一张桌子上有两个炉子测定有机物中的氮。他一边观察着物质的燃烧情况,一边点着另一个炉子,接着准备下一个试验所需用的坩埚和有机化合物,他显得熟练而得心应手。到了傍晚,五项分析都做好了。库尔蒂乌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赞叹道:“您真是个魔术家!”
“关键在于统筹,亲爱的朋友。”费舍微笑着说。
也许费舍说得对。但是,尽管其他人也都很勤奋和努力,并且学着他“统筹”安排,可是在实验技术上谁也比不上费舍。他总是几项课题齐头并进,几个试验同时动手。 臭气冲天
艾米尔?费舍在慕尼黑实验室首先搞的研究工作是醛的苯腙试验,他把苯肼作用于丙醛,取得一种晶体,这种晶体与粪臭素在成分上稍有区别,仅在于这种晶体的分子比粪臭素还多一个氮原子和三个氢原子。
“如果我能把这多余的原子分离出去,那么肯定就可以制得粪臭素。”
“您用什么方法呢?”拜尔教授问他。
“热分解,加入了各种催化剂都没有奏效。”
“加入酸类也不行吗?”
“不行。”
“您用锌粉和锌盐试一试,”拜尔教授建议说。
加入锌粉毫无结果。不过,锌盐之一的氯化锌却显得很有活性。费舍继续给它们加热。这时,烧瓶里冒出一股味来。
“迪克,这是什么东西?你好像把整个王国的马粪都收罗来了!”实验室里的另一个实习生大叫起来,并且拼命地用手在鼻子前扇着。但这股臭味太浓厚了,连大马力的通风机都吹不散。
“成功啦!”费舍喊道,毫不在意大伙儿的嫌恶表情。
但是,谁也不听他那欣喜若狂的话。大家熄了各自的燃烧炉,停止试验,争先恐后地从实验室里跑了出去,只有费舍还呆在臭气冲天的屋子里继续工作。
艾米尔相信,继续研究下去还会有新的发现。他的衣服、头发和皮肤上沾满了粪臭素的气味,他毫不介意。
实习生们渐渐地也对这个臭味习以为常了。不过,无论他们上街,吃饭、看戏,不管到哪儿去,这股气味都阴魂不散地跟着他们。
“我们可让胖费舍害惨了!”
艾米尔的情况更糟。他是个音乐迷,城里举行音乐会或演出歌剧,他总会抽出时间到场,可是现在,这股气味却把他搞得很狼狈。
一天,他去看歌剧,刚刚坐定,就看见人们看他的眼光不对劲,邻座的观众掏出手帕,还互相咬耳朵,有位女士则干脆掏出了香水瓶。
“谁把这个马给放进剧场来了?”有人大声喊着。
艾米尔脸红了,赶忙逃离了剧场。他十分认真地洗了澡,换上了衣服,但那股令人厌恶的臭味仍从他的皮肤里散发出来,紧随不散。
“没关系,”拜尔教授安慰他说,“搞科学研究是要付出代价的,这还不算是什么重大的代价。何况你已经做出了发现。”
艾米尔只有苦笑,不过,尽管如此,他也决不会放弃他心爱的科学研究的。
“女巫式的预言”
1878年,艾米尔获得了副教授的学衔。这一年,他和堂兄奥托一起研究碱性副品红,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搞清楚了碱性品红和碱性品红的结构。
当时,慕尼黑的艺术家们常常在市内最宽敞的大厅中举行联欢会。有一次,艾米尔和另一位青年科学家哥尼希斯应邀参加了一次大型的联欢会。
巧妙的艺术装饰把大厅变成一座引人入胜、富丽堂皇的宫殿。来宾们身着色彩缤纷的华贵礼服。艾米尔和哥尼希斯衣着朴素,不惹人注意,他们可以悠闲地观赏大厅里进行的联欢活动。
“你估计皮尔海姆今天会是什么穿戴?”哥尼希斯问费舍。
“王子的装束。”
皮尔海姆是慕尼黑城内一位大名鼎鼎的艺术家。
衣饰华丽的人群突然闪动起来,让出一条通道。皮尔海姆在待从们的簇拥下,步入大厅。他身着天鹅绒与丝绸做成的盛装,光彩夺目,果真像个王子。他频频招手致意着,来宾们则向他深深鞠躬行礼。这一支队伍还没有走到大厅的尽头。对面门口又出现了一位在侍从们前护后拥下的王子。
“瞧”,费舍用胳膊肘触了一下哥尼希斯,“这才是真王子呢,威廉?巴伐尔斯基王子。”
他们都穿着华丽的丝绸物,一同去观看表演了。
联欢会的精采节目是一群“爱斯基摩人”的表演,演员们穿着用粗毛和破麻絮制作的衣服,在用树皮搭成的帐逢旁跳着一种怪模怪样的舞蹈。其它装饰和道具也都是用这种易燃材料做成的。
费舍忧虑地看了看四周,说:“人们都在吸烟,我担心会有什么东西突然着起火来。这些有机物太容易着火了。”
哥尼希斯说:“别瞎操心了。走吧,到小吃部里喝点啤酒吧。”
但事实被费舍不幸言中了。他们的一杯酒还没喝完,大厅里就传来了惊叫声:“着火啦!”
“爱基斯摩”人的衣服全着火了,他们像一条条火龙,在大厅中翻腾,燃着了周围的一切。来宾们吓得魂飞魄散,争向门口狂奔。快乐的节日气氛荡然无存。
“你做了个女巫式的预言。”哥尼希斯心有余悸地对费舍说了一句。 “造出咖啡”
费舍作为一个有机化学家,并没有把兴趣局限于有机化学领域,他很想知道动物机体内所发生的各种生物学过程和生物化学过程。
“动物机体是一座万能实验室。”费舍对他的助手克诺尔说,这时候他已是化学教授。那里合成的物质多得不可胜数!人类早就渴望揭示这些变化过程的本质,可是,我们现在距离了解真相还十分遥远,有两种方法可以揭开这些秘密:或者研究有机体进行生命活动时所产生的分解产物,即有机体的排泄物,或者合成出那些本来是由活细胞所制造的物质。”
在实现这一任务方面,化学取得相当大的成就,但还有许多重大的问题未能解决。其中,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对蛋白质和蛋白质新陈代谢的研究,在人和温血动物身体内,蛋白质进行分解,分解的最终产物是尿素,而“冷血”动物和鸟类,身体内进行的新陈代谢则产生尿酸。
艾米尔?弗舍选择了尿酸作为研究对象。
为了确定尿酸及其衍生物的准确结构,需要合成这些物质的各种各样的衍生物,需要把它们从天然产物中分离出来。
费舍在这一探索过程中,做出了十分重要的发现。他用五氯化磷处理有机酸,得到了相应的氯化物,它们具有较强的反应能力并易于转变为酸的衍生物。费舍就这样从尿酸中制得了三氯嘌呤,并用苛性钾与碘化氢对三氯嘌呤继续处理,制得黄嘌呤,将黄嘌呤甲基化之后,制得了咖啡硷??一种无色、味苦的晶体,它通常在咖啡豆和茶叶中。而现在费舍把它合成出来了。
合成的咖啡硷同天然的咖啡硷完全一样,也具有相同的兴奋作用。
费舍特意把朋友们请来,开了一个小小的“咖啡宴”。
“现在,我请你们喝不用咖啡做的咖啡。”费舍从厨房里出来对朋友们说道。他端着一只小金属杯,一股咖啡香味飘满了屋子。他把饮料斟进茶杯里,请朋友们品尝。
“我信服化学的威力,也信服我们迪克厨师的手艺!”哥尼希斯说着端起茶杯,呷了一口。他在嘴里噙了一会儿,仔细品味一番才咽下去,一本正经地说道:“如果德国有朝一日没有了咖啡,迪克,你一定会成为最有钱的人。你的产品会供不应求的!” 一见钟情
费舍的杰出成就闻名于世,国内外有很多大学邀请他前往任教。
经过考虑,费舍选择了爱尔兰根。它虽然是个不大的城市,但是,它刚刚为大学盖了新楼,实验室的设备也比较齐全,因此,费舍选择了它。
朋友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会,学生们依依不舍地与他们爱戴的教授告别。
费舍只携带了随身的必需品,就搭上了开往爱尔兰根的火车。
车厢的单间里原来只有他一个人,火车到纽伦堡时,进来一位美丽的年轻姑娘,由一位看来是她父亲模样的老人陪着。老人向费舍打了个招呼,并自我介绍说:“雅科布?冯?盖尔拉赫教授。”
费舍躬身还礼,也作自我介绍。
“常听我的堂兄恩斯特?费舍提起您。我的堂兄也是一位解剖学家。很高兴同您,爱尔兰根的科学家认识,我也正要到那里去。”
两位教授就他们共同感兴趣的问题热烈地交谈起来。
盖尔拉赫的女儿阿格涅斯细心地倾听着他们的谈话,她怎么能想到,这位萍水相逢而且比她年长许多的人,几年以后竟会是她的丈夫呢。
费舍只顾和盖尔拉赫教授津津有味地交谈,对这位美丽的动人的小姐几乎没有留意。虽然,过去他常参加一些聚会和联欢会,却完全不善于同女性打交道,尽管他通晓音乐、戏剧、绘画,谈起话来妙趣横生,但一和女性相处,他就会觉得拘束起来。
对这位美丽的小姐也是一样,费舍感到只有滔滔不绝地和盖尔拉赫教授交谈下去,才可以摆脱教授女儿给他带来的困窘,然而他内心里却也生出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很想和她亲近似的。
不知道自己已经对这位美丽的姑娘一见钟情了,在以后繁忙的科研之余,当他一身独处时,就愈来愈想念在火车上遇到的这位红颜佳人。
当然,后来他们如愿以偿地举行了婚礼,成为美满幸福的一对。 化学家的口才
阿格涅斯给费舍带来了温暖和幸福,他们的生活充满乐趣,不久,费舍应邀出任符次堡大学的化学教授,他们全家搬到了符次堡。
符次堡的生活轻松愉快。除了听音乐会、参观展览会和游览等消遣之外,按惯例,学术界每逢节日轮流到各教授家中聚会,谁也记不清这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惯例。但大学都严格遵守。通常,出席集会的有医生、植物学家、哲学家、物理学家和化学家。集会上最隆重的时刻莫过于由一位来宾致贺词了,如果贺词充满幽默,那可真是满室生辉的时刻。
一次,在一位教授科尔劳什家举办的集会上,由费舍致欢迎词。当然,演讲内容他率先已经考虑好了。他从主人科尔劳什研究多年的电学谈起,继而把话题转入不久前出现的电灯。“那种灯光柔和而充满了圣洁的光辉,就像在座的各位容光照人的女士发出来的,而我们美丽动人的科尔劳什夫人,则可与光辉灿烂的电弧相媲美!”
这篇演讲获得了极其热烈的掌声,费舍坐下来后,邻座的哲学教授赫寒尔俯身对他低声说:“现在我才知道,你们化学家的口才远远超过哲学家。”
“过奖过奖。”费舍得意地笑了笑。 就职的条件
费舍作为一位有机化学领域中出类拔萃的实验家和大理论家的声望引起了许多大学的重视。聘书从亚琛、苏黎世、海德堡、柏林接踵而来。费舍不愿离开符次堡,但阿格涅斯和她父亲执意劝他接受柏林的邀请。
“这个教授职位可是德国所有大学中最优越的职位。”阿格涅斯说,“何况,柏林又是首都。”
“这不仅是一种荣誉,而且是对你学识的一种承认。”她的父亲赞同说,“承认你是德国卓越的科学家。拒绝应聘等于宣布你不敢担当我国化学界的泰斗。不能拒绝,艾米尔,你好好想想自己的条件,然后把这些条件向部里提出来。如果他们确实器重你,就会接受你的条件,那时你就可以按自己的愿望安排了。”
老费舍也劝儿子接受柏林的邀请。于是,艾米尔?费舍经过仔细考虑后向部里提出自己的条件:现在的研究所大楼已不能适应现代大规模实验工作需要,因此,必须修建和装备新楼。同时,楼内房间的布局应当便于实验工作。
“可是我们一定会遭到财政部的坚决反对的!柏林大学过去在化学方面做出不少发现,也并没有增加任何新设备。要求盖新楼,恐怕我提不出足够的理由来为您的建议辩护。”部里的顾问表示反对。
“这是我必不可少的条件,否则,我宁愿留在符次堡。”
化学家的声誉和成就起了作用,谈判结果,部里的代表答应为化学研究所盖新楼,于是,费舍接受了邀请。 神通广大的实验室
费舍在嘌呤类化合物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阐明了糖类结构,合成出葡萄糖、果糖及其他单糖,他因此而获得了1902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研究糖类和分离糖类积累起来的经验也用来研究蛋白质,不过,此项工作要比糖类复杂得多。
但费舍和他的助手们还是毅然决定向这个困难进军。
实验室的工作热火朝天地展开了。他们对蛋白质进行水解,最后制得了一种氨酸,这种氨酸稍有甘味,因此他们命名为甘氨酸。
经过多次改变试验条件,他们又进一步制出了甘氨酰甘氨酸,费舍把这种新物质命名为肽,确切地说,应称为二肽。
“下一步的试验目的是合成更为复杂的分子??三肽、四肽、多肽……”费舍对助手们说。
试验进行得很缓慢,一种试验不得不重复多次。但最后,他们成功地合成出了多肽分子。
这项实验成功的消息,不仅震动了科学界,全人类都为之欢欣鼓舞!
《维也纳日报》上出现了一篇耸人听闻的文章:“在试管中合成蛋白质!”这条新闻成了星星之火,顿时引起报界的哄动,记者们极尽想象杜撰之能事,连幻想家也自愧不如了。他们认为,地球上人类食物的供应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他们描绘出一幅图景,仿佛在艾米尔?费舍“神通广大的实验室”里,能够把煤变成美味可口、营养丰富的佳肴。
费舍被这些消息搞得哭笑不得。是的,他确实找到了合成氨基酸的方法,但进行这项实验的代价极高,而步骤又非常繁多,因此根本还谈不上生产人造食品的问题。
但是,就这已够这位科学家荣耀的了。他为人类做出了一步伟大的发现,足以使他彪柄史册,名重万代。
1916年,六十四岁的费舍开始埋头撰写他的最后一部巨著??自传。但他的身体状况却变得越来越糟糕。三年后,医生查出他得了不治之症??癌症。
费舍清楚地意识到等待他的是什么,但他毫不畏惧死亡。他从容地把他的一切事务都安排妥当。完成了著作手稿,把自传赶写完毕,但是,这位化学家没来得及看到它的问世。 1919年7月15日,艾米尔?费舍与世长辞了。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http://www.jiyifa.net/gaozhong/791340.html
相关阅读:高考必备:如何进行化学实验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