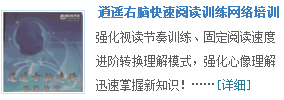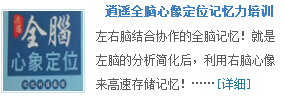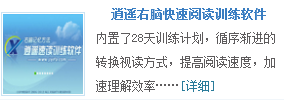▲张益唐与《素数间的有界距离》。
数学家张益唐对美有着执着的追求。
他喜欢在休息时听西方古典音乐,还钟爱文言文的精炼之美,正如他热爱数论的美一样,因为“美都是相通的”。
他最好的朋友几乎都是艺术家,譬如指挥家齐光。在齐光家后院的“灵光一现”,让他找到了解开“孪生素数”猜想难题的钥匙,亦改写了自己的人生。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数学教授爱德华·弗伦克尔称张益唐破解这一难题的证明有“文艺复兴之美”。
猜想之后
美国科罗拉多州普韦布洛的夏天干燥而炎热。
下午两点,张益唐一人在指挥家朋友齐光家的后院来回踱步,他希望看到梅花鹿一家像往常一样到后院的两棵树下乘凉。
他总是习惯于在散步时思考数学问题,似乎这样比静止时更有效。
不过,这一次鹿没来,灵感却不期而至。
“关于‘孪生素数猜想’关键的一点突然一下想通了。”他说,过去他苦苦探索,从至少三个方向去破解问题,这一刻找到了将三个方向联结在一起的路。
他没用纸笔记录,也并未告诉任何人,依旧按计划赶去听齐光为美国独立日公开音乐会所做的彩排。他全心全意听完一场演奏,刚才激动人心的发现被“全部放下”。
回到学校后,他将所思整理成论文《素数间的有界距离》,投给数学界顶级期刊《数学年刊》。论文被审稿严苛的期刊“火线”接受,仅用两周。
素数(也叫质数)是数论中的基础概念,指只能被1和它本身整除的数,如2、3、5、7等。如果两个素数之间的差正好等于2,它们就是一对孪生素数。“孪生素数猜想”是数论中的著名的“未解之谜”,认为存在无穷多对孪生素数。但随着数字的增大,孪生素数在数轴上的分布越来越稀疏,这时再寻找孪生素数无异于“大海捞针”。
张益唐的突破就在于利用一种创新性的筛法,把孪生素数间的距离从无限缩小至有限。他证明了在数字趋于无穷大的过程中,存在无穷多个之差小于7000万的素数对。
英国《自然》杂志称张益唐的工作为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如今,全世界数学家在张益唐成果的基础上继续缩小这个距离数。获得有数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茨”奖的华裔数学家陶哲轩为此设立全球性项目,研究团队目前将无穷多个素数的差缩减到246。
“目前来看是最小,原则上还可能再缩小,但难度会越来越大。要得到更好的结果,牵涉到理论计算的东西就越来越复杂。”张益唐说。
成名后的两年,场场讲座、媒体采访令他应接不暇,有时甚至想着“还不如不出名”。最近,关于孪生素数的研究似乎“冷了一点”。“也许过一阵子就又热了。”他说,手边还有很多数论方面的“半成品”工作继续在做。
初,张益唐来到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数学系任教。尽管尚未开始正式带学生,他身边逐渐聚集了一些学生共同做研究。比起前些年的踽踽独行,他比较满意现在的状态。
当记者问起是不是希望有人继承衣钵,他笑道:“衣钵的前提是自己是个宗师,但我还不是宗师,没那么了不起。但自己的一些发现,至少希望还有别人能了解,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做下去。”
三次转折
年少多磨,暮年成名,张益唐称自己的人生有三次转折。
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本科是第一次,他随后师从著名数学家、北京大学潘承彪教授攻读硕士学位,“这为我打下了做学问的基础,做学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没有扎实的基本功不行。”
1985年,张益唐赴美国普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学术生涯开始历经坎坷。“具体我不太想多说了。”他的表情变得有些严肃,只说是“多方面的原因”,但不否认和导师有关。
在普渡大学,他的导师是台湾代数专家莫宗坚。当时,张益唐选择“雅可比猜想”作为博士论文,他只用了两年就得出部分成果,但时隔五年才拿到博士学位,论文未能发表,他也没拿到导师的推荐信。张益唐无法继续融入学术圈,无奈漂泊各州。
在美国中部肯塔基州的小城市莱克星顿,张益唐得到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在朋友的Subway快餐店做会计。工作之余他继续研究数学,也并不觉得辛苦,因为“总觉得自己还是能够回到学术上去的,总觉得自己应该还有机会。”
第二次转折在1999年到来,在老同学的推荐下,张益唐在新罕布什尔谋得一份教授微积分的讲师职位。尽管只是编外,但能够重新“找到工作继续做学问”让他很高兴。
直到第三次转折出现——关于孪生素数的论文发表在《数学年刊》——张益唐才真正被主流学术界所认可。2013年论文正式发表时,他已58岁。
“我当时心里很淡定,并没有特别高兴,情绪上起伏没那么大,可以说是释然了吧。”张益唐说,“如果年轻时成名,无非好运气早来几十年,对我来讲没有太大区别。”
相反,他称太太可能“感受更加强烈”,如果对他自己来说这是意料之中,对太太来说则完全是意料之外。
2000年,张益唐在纽约的一家餐厅经朋友介绍见到太太孙雅玲,他欣赏她“心地善良、好强自立”。她不懂数学,不太了解张益唐具体在研究什么,更没想到他会出名。当文章引起一定轰动后,他才打电话告诉太太,而太太的第一句话竟是:“你是不是喝多了?”
“我在成功之前从不愿意多说什么,这会让她认为这个男人夸夸其谈。所以尽管我一直都觉得自己会成功,她却从未多想,所以对她来说是很大的惊喜。”张益唐说。
数字敏感
似乎很多数学家都是天赋异禀。张益唐在生活中也有着特殊的数字敏感。在采访中,他能清晰地复述跟数字有关的任何事,无论时隔几年或是几十年。
“遇到一个数,我常常自然地去看是几的倍数,或是是几的几次方,看得比较准。”他说。他手机里甚至没有通讯录,“我很少跟人通话,一般朋友的电话都是记在脑子里。”
张益唐对数学的兴趣来自于小学时读的科普读物《十万个为什么》,他依然记得全套八册书中的最后一册是数学,讲了高斯等很多大数学家的故事。前几年他在朋友家看到最新一版,特意又翻阅了一下。
他承认数学一直是自己从小到大最好的科目,“小时候我就喜欢做难一点的题目,因为比较有挑战。”有时他会觉得老师的解题思路还没有自己好。
在他看来,中国学生做学问需要更大的气魄和胆识,要敢于质疑,“完全跟着老师走,不敢超越老师,是不能造就第一流的科学人才的。”
“我发现中国留学生有个问题,他们从来不提问,但美国学生就没有这方面顾虑,他们发言特别踊跃,敢于说话。中国学生顾虑太多,总是怕一开口就说错。可是做学问有什么对错呢?”他说。
张益唐认为,不同领域里有越来越多的华人数学家正在崛起,尽管整体水平跟欧美、日本等国还有差距,但年轻一代数学家将来还是大有希望。只是,“他们需要更多挑战性的思考。”
张益唐手边放着几页写满公式的演算纸,等着与即将来访的研究生们讨论。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给了他一间办公室,邀请他每年回国两个月讲学和做研究。北京闷热的夏天让他不想出门,更愿“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这样安静的环境让我更好地思考,我也享受孤独的状态,这是肯定的。”他说。他习惯早睡早起,晚上十点睡,早上五六点醒。一天用在数学研究上的时间,多时可达十几个小时,但真正坐在办公桌前下笔写却不多,大多数时间都用在了思考上,“一天到晚一直想着也不会累。”
他经常随身带着那本改变他人生轨迹的论文《素数间的有界距离》,“有时总要拿出来翻一翻,看一看。”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http://www.jiyifa.net/gaozhong/793574.html
相关阅读:让数学知识生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