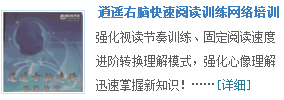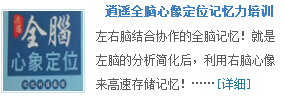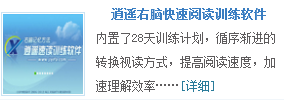作者:中山纪念中学 郭跃辉
言语形式,是语言在语境因素下的具体运用形式。它与言语内容是相对应的概念,言语内容就是语言在语境中产生的意义。对于教材文本而言,言语内容就是语言在具体文本中表达的意义,而言语形式就是语言在具体文本中的表现形式。前者侧重于“文本表述的内容”,后者则是“如何表现文本的内容”。对于文本而言,决定言语内容的往往是某些关键的言语形式点,这些关键点也是作者的艺术匠心所在。抓住言语形式的关键点,可以深入有效地解读文本,取得“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具体说来,言语形式的关键点,指的是言语形式的矛盾点、重复点和炼字点。
一、言语形式的矛盾点
矛盾,在文学理论中也被称为悖论、诡论、吊诡,即文本与生活、文本与文本的矛盾之处,用美国“新批评”文论家布鲁克斯的话说就是:“表面上荒谬而实际上真实的陈述。”“荒谬”与“真实”构成悖论。孙绍振教授在阐述“矛盾还原法”时分析:“我的还原,只是为了把原生状态和形象之间的差异揭示出来,从而构成矛盾,然后加以分析,并不是为了去蔽,而是为了打破形象天衣无缝的统一,进入形象深层的、内在的矛盾。”
《诗经·静女》中有一句诗:“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这句话表面看没有什么奇特之处,但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就会发现“矛盾”。“俟我于城隅”,即以男子的口吻讲有一位姑娘在城隅等“我”,那“我”是如何得知的?很显然,二人之前一定有过约定,而且是女子主动跟男子说:“某某时间我将在城隅等你”,这样,男子才会如期赴约,并且自豪而忐忑地说:“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俟我于城隅”隐含着一种表述,即是女子主动约会男子的,如果是男子主动的话,那表述方面就应该是“我在城隅等姑娘”,也就是说,肯定是女子主动说“我在哪哪等你”,并且先于男子到达,这位憨厚的男孩子才会说“俟我于城隅”。这位漂亮活泼而又调皮大胆的女孩子,不仅主动约会男子,而且主动等待男子,更重要的是主动赠送男子礼物,这种行为也只有在礼教最薄弱的时代才会有,这也正是先民们真实的生活状态。
沈从文的小说《边城》中,故事开篇,并不是以主人公为线索,跟随主人公的行踪叙述事件,而是继续围绕茶峒的风俗人情展开。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叙述到此地的民风时,用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莫不”,例如:“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端午日,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在城里住家的,莫不倒锁了门”,“因为这一天军官税官以及当地有身分的人,莫不在税关前看热闹”。当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词就是“全”“一律”,这些词都是“全称副词”,表示“都”。于是一个问题出现了:作者在写这个地方的风俗时,为什么用到这么多的全称副词?难道这个地方的人都行动一致,心就那么齐?这显然是与实际生活不符。其实,作者通过这些略带夸张的全称副词,表现的是一种人们的生活心理与生活方式的相通性。正因为心意相通,才会互相理解,关系才会融洽。
王维的《山居秋暝》有一个核心的矛盾:空与不空。诗歌开篇就说“空山新雨后”,点出了“空”字,但是随着诗意的展开,我们发现王维隐居的山并非真正的“空山”,而是一个充满了生活情趣的所在。这里不仅有潺潺的清泉,还有处于日常生活状态下的普通人,她们要么去洗衣,要么去采莲,抑或是捕鱼,正是一派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的图景。既然如此,作者为什么说是“空山”呢?其实,王维崇尚佛法,追求空明宁静,喜欢隐居在安静的环境中,但是他毕竟不是和尚,不是高僧,而是一个诗人。他不是用禅宗的眼光来观察这个世界的,而是用诗人的审美眼光来审视这个世界的。王维内心是有着深沉的“人间情怀”的,他绝对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得道上人。因此,他的诗歌中充满着浓浓的生活气息,他的诗歌说到底也是人间百态的鸣奏曲。
矛盾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矛盾的主体最终达到深层次的统一。发现文本的矛盾,并且对矛盾进行解剖,最终使得矛盾冲突变成和谐统一,这就是解读文本时发掘矛盾价值的途径。
二、言语形式的重复点
重复,就是作者有意识地反复使用某些词,起到抒发强烈感情、加强语势的作用。重复,并非语法上的赘余,而是有意识地对语言进行变形化处理。这些重复点,往往是理解作者内心世界的关键,是理解整个文本的关键。
巴金的《小狗包弟》,从言语形式上讲,本文出现了大量的“我”和“自己”,甚至在没必要出现“我”的地方,作者也用了“我”这个第一人称代词。例如:
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一方面责备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让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堕入地狱。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
从想象包弟被解剖,联想到自己的灵魂也在被解剖,作者感到“羞耻”,“瞧不起自己”,其实就隐含着一种痛彻心肺的忏悔。作者有时用“我”,有时用“自己”,有时连用为“我自己”,如此众多的表示第一人称的词,不仅说明了作者内心的复杂,想法众多,心情多样,急切地想要表达内心丰富的情感,乃至有一种“语无伦次”之感,同时,这众多的第一人称代词,有对自己的指责,有对自己的批评,也有自己的忏悔,这是一种直面人生的勇敢,也是一种人生的深刻自省。
无独有偶,陆蠡的《囚绿记》,这篇文章用到的“我”特别多,经统计,文章有84处出现了“我”字,特别是在第5段和第8段,“我”轰炸式的出现,肯定不是没有原因的。其实,将这两段中三分之一的“我”去掉,丝毫不影响文章的表达,甚至能让文章更为简明清晰。那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例如第八段,教师可将不必要的“我”字都去掉,请学生比较分析二者的区别,然后去体会“我”从审美观照的“爱”向“自私占有”的爱的过渡与转变。去掉“我”之后,感情似乎没有这么强烈了。用了这么多“我”,好像很急切,急切地占有眼前的绿叶,而且感情很强烈,是一种强烈的主观意愿。这一小段话,用了以“我”为开头的句子,一连用了三个,而且短短几句话,出现了7个“我”,这就可以看出作者此时强烈的主观性,同时也照应了本段开头的“忽然有一种自私的念头触动了我”。
一般说来,感情冲动、强烈的时候,往往会重复使用某些词,这些词就是理解文本主旨的关键。当然,言语形式是表达一定的言语内容,如果对言语内容的表述没有起到一定的作用,这种重复就是语法错误了。
三、言语形式的炼字点
文章写作,特别是文学创作,是一个精神性的创造过程。这种创造性不仅体现在文本主题的深刻、形式的新颖,还体现在语言的运用上。古人就有“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之说。类似的诗歌炼字的佳话,数不胜数。诗歌如此,其他文体的创作也是如此。
杜牧在《阿房宫赋》里有一句话:“二川溶溶,流入宫墙”,其中的“入”字常被人忽视。将这两句改为“二川溶溶,流入大海”,感觉没意思,因为与阿房宫没有直接的关系。改为“二川溶溶,流过宫墙”,感觉味道不足。流过,说明阿房宫是建造在渭河和樊川边上,没什么奇特的。但如果说“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两条大河,相距不可能很近,居然流入了阿房宫,那么阿房宫构建之奇、规模之宏,由此可见一般。“溶溶”,粤教版教材注释为“水流缓慢的样子”,人教版教材注释为“水势浩大的样子”,比较而言,后者的解释更有艺术性,更能衬托出阿房宫的特点。
柳永的《雨霖铃》中有句词:“骤雨初歇”,一个“初”字说明暴雨刚刚停止,天上不可能有夕阳,不可能有晚霞,而只能是阴冷,这样,在一个阴冷的黄昏,听着蝉凄切的哀鸣,这种环境,这种氛围,被作者渲染到极点。还有,主人公显然不想离别,想永远和恋人待在一起,但是总是要离别。正在这时,天下起了暴雨,主人公心情肯定很高兴,因为终于找到了一个放弃离别的客观理由了,所谓“人不留客天留客”:不是我不想走,而是雨太大了,自己无法离开。但是一个“歇”字打断了主人公的美梦。骤雨停止了,主人公再也没有滞留的理由了,那内心的痛楚与失落可想而知。
王昌龄的《从军行》有一句诗:“黄沙百战穿金甲”,一个“穿”字,堪称神来之笔。我们试想一下,如果边关将士生活在像春雨江南那样的环境中,金甲能“穿”吗?显然不能,这就说明了边关环境之恶劣,风沙之大;进一步想,即使风沙很大,那如果将士们整天待在屋子里不出来,那金甲能“穿”吗?显然也不能,这说明将士们需要进行野外活动。再想一下,即使是野外活动,如果偶尔穿着盔甲出来走走,黄沙能把金甲磨穿吗?显然也不能,必须是经常在户外活动。再退一步想,即使是经常在户外活动,即使有风沙,那需要多大的风沙才能将金甲磨穿?这也暗示出风之大,沙之多。如果没有战争,金甲也不可能“穿”,这也说明了战争之频繁、战争之惨烈。
炼字,并非考试意义上的炼字,即按照一定的格式和程序进行的答题规范,而是要深入到文本内部,运用“换词法”,体会字的精妙之处。
当然,言语形式的矛盾点、重复点和炼字点,相对于博大精深的言语形式来讲,只能算是恒河沙之一粒。而只有在关注文本的言语内容的同时,也注意到言语形式的特殊之处,对文本的理解才能更加深入,对作者的艺术创造的功力,也多一份认可。
作者:中山纪念中学 郭跃辉
言语形式,是语言在语境因素下的具体运用形式。它与言语内容是相对应的概念,言语内容就是语言在语境中产生的意义。对于教材文本而言,言语内容就是语言在具体文本中表达的意义,而言语形式就是语言在具体文本中的表现形式。前者侧重于“文本表述的内容”,后者则是“如何表现文本的内容”。对于文本而言,决定言语内容的往往是某些关键的言语形式点,这些关键点也是作者的艺术匠心所在。抓住言语形式的关键点,可以深入有效地解读文本,取得“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具体说来,言语形式的关键点,指的是言语形式的矛盾点、重复点和炼字点。
一、言语形式的矛盾点
矛盾,在文学理论中也被称为悖论、诡论、吊诡,即文本与生活、文本与文本的矛盾之处,用美国“新批评”文论家布鲁克斯的话说就是:“表面上荒谬而实际上真实的陈述。”“荒谬”与“真实”构成悖论。孙绍振教授在阐述“矛盾还原法”时分析:“我的还原,只是为了把原生状态和形象之间的差异揭示出来,从而构成矛盾,然后加以分析,并不是为了去蔽,而是为了打破形象天衣无缝的统一,进入形象深层的、内在的矛盾。”
《诗经·静女》中有一句诗:“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这句话表面看没有什么奇特之处,但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就会发现“矛盾”。“俟我于城隅”,即以男子的口吻讲有一位姑娘在城隅等“我”,那“我”是如何得知的?很显然,二人之前一定有过约定,而且是女子主动跟男子说:“某某时间我将在城隅等你”,这样,男子才会如期赴约,并且自豪而忐忑地说:“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俟我于城隅”隐含着一种表述,即是女子主动约会男子的,如果是男子主动的话,那表述方面就应该是“我在城隅等姑娘”,也就是说,肯定是女子主动说“我在哪哪等你”,并且先于男子到达,这位憨厚的男孩子才会说“俟我于城隅”。这位漂亮活泼而又调皮大胆的女孩子,不仅主动约会男子,而且主动等待男子,更重要的是主动赠送男子礼物,这种行为也只有在礼教最薄弱的时代才会有,这也正是先民们真实的生活状态。
沈从文的小说《边城》中,故事开篇,并不是以主人公为线索,跟随主人公的行踪叙述事件,而是继续围绕茶峒的风俗人情展开。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叙述到此地的民风时,用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莫不”,例如:“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端午日,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在城里住家的,莫不倒锁了门”,“因为这一天军官税官以及当地有身分的人,莫不在税关前看热闹”。当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词就是“全”“一律”,这些词都是“全称副词”,表示“都”。于是一个问题出现了:作者在写这个地方的风俗时,为什么用到这么多的全称副词?难道这个地方的人都行动一致,心就那么齐?这显然是与实际生活不符。其实,作者通过这些略带夸张的全称副词,表现的是一种人们的生活心理与生活方式的相通性。正因为心意相通,才会互相理解,关系才会融洽。
王维的《山居秋暝》有一个核心的矛盾:空与不空。诗歌开篇就说“空山新雨后”,点出了“空”字,但是随着诗意的展开,我们发现王维隐居的山并非真正的“空山”,而是一个充满了生活情趣的所在。这里不仅有潺潺的清泉,还有处于日常生活状态下的普通人,她们要么去洗衣,要么去采莲,抑或是捕鱼,正是一派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的图景。既然如此,作者为什么说是“空山”呢?其实,王维崇尚佛法,追求空明宁静,喜欢隐居在安静的环境中,但是他毕竟不是和尚,不是高僧,而是一个诗人。他不是用禅宗的眼光来观察这个世界的,而是用诗人的审美眼光来审视这个世界的。王维内心是有着深沉的“人间情怀”的,他绝对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得道上人。因此,他的诗歌中充满着浓浓的生活气息,他的诗歌说到底也是人间百态的鸣奏曲。
矛盾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矛盾的主体最终达到深层次的统一。发现文本的矛盾,并且对矛盾进行解剖,最终使得矛盾冲突变成和谐统一,这就是解读文本时发掘矛盾价值的途径。
二、言语形式的重复点
重复,就是作者有意识地反复使用某些词,起到抒发强烈感情、加强语势的作用。重复,并非语法上的赘余,而是有意识地对语言进行变形化处理。这些重复点,往往是理解作者内心世界的关键,是理解整个文本的关键。
巴金的《小狗包弟》,从言语形式上讲,本文出现了大量的“我”和“自己”,甚至在没必要出现“我”的地方,作者也用了“我”这个第一人称代词。例如: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http://www.jiyifa.net/gaozhong/948910.html
相关阅读:浅析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