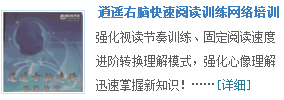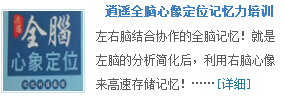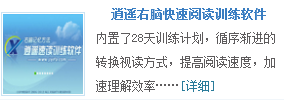王充论衡?卷二十七?原文及翻译
王充论衡?卷二十七?定贤篇原文
圣人难知,贤者比於圣人为易知。世人且不能知贤,安能知圣乎?世人虽言知贤,此言妄也。知贤何用?知之如何?
以仕宦得高官身富贵为贤乎?则富贵者天命也。命富贵不为贤,命贫贱不为不肖。必以富贵效贤不肖,是则仕宦以才不以命也。
以事君调合寡过为贤乎?夫顺阿之臣,佞幸之徒是也。准主而说,适时而行,无廷逆之郄,则无斥退之患。或骨体?丽,面色称媚,上不憎而善生,恩泽洋溢过度,未可谓贤。
以朝庭选举皆归善为贤乎?则夫著见而人所知者举多,幽隐人所不识者荐少,虞舜是也。尧求,则咨於鲧、共工,则岳已不得。由此言之,选举多少,未可以知实。或德高而举之少,或才下而荐之多。明君求善察恶於多少之间,时得善恶之实矣。且广交多徒,求索众心者,人爱而称之;清直不容乡党,志洁不交非徒,失众心者,人憎而毁之。故名多生於知谢,毁多失於众意。齐威王以毁封即墨大夫,以誉烹阿大夫。即墨有功而无誉,阿无效而有名也。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孔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曰:“未可也,不若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夫如是,称誉多而小大皆言善者,非贤也。善人称之,恶人毁之,毁誉者半,乃可有贤。
以善人所称,恶人所毁,可以知贤乎?夫如是,孔子之言可以知贤,不知誉此人者贤也?毁此人者恶也?或时称者,恶而毁者善也?人眩惑无别也。
以人众所归附、宾客云合者为贤乎?则夫人众所附归者,或亦广交多徒之人也,众爱而称之,则蚁附而归之矣。或尊贵而为利,或好士下客,折节俟贤。信陵、孟尝、平原、春申,食客数千,称为贤君。大将军卫青及霍去病门无一客,称为名将。故宾客之会,在好下之君。利害之贤,或不好士,不能为轻重,则众不归而士不附也。
以居位治人,得民心歌咏之为贤乎?则夫得民心者,与彼得士意者,无以异也。为虚恩拊循其民,民之欲得,即喜乐矣。何以效之?齐田成子、越王勾践是也。成子欲专齐政,以大斗贷、小斗收而民悦。句践欲雪会稽之耻,拊循其民,吊死问病而民喜。二者皆自有所欲为於他,而伪诱属其民,诚心不加,而民亦说。孟尝君夜出秦关,鸡未鸣而关不,下坐贱客,鼓臂为鸡鸣,而鸡皆和之,关即启,而孟尝得出。〔夫〕鸡可以奸声感,则人亦可以伪恩动也。人可以伪恩动,则天亦可巧诈应也。动致天气,宜以精神,而人用阳燧取火於天,消炼五石,五月盛夏铸以为器,乃能得火。今又但取刀剑铜钩之属,切磨以向日,亦得火焉。夫阳燧、刀、剑、钩能取火於日,?非贤圣亦能动气於天。若董仲舒信土龙之能致云雨,盖亦有以也。夫如是,应天之治,尚未可谓贤,况徒得人心,即谓之贤,如何?
以居职有成功见效为贤乎?夫居职何以为功效?以人民附之,则人民可以伪恩说也。阴阳和、百姓安者,时也。时和,不肖遭其安;不和,虽圣逢其危。如以阴阳和而效贤不肖,则尧以洪水得黜,汤以大旱为殿下矣。如功效谓事也,身为之者,功著可见。以道为计者,效没不章。鼓无当於五音,五音非鼓不和。师无当於五服,五服非师不亲。水无当於五采,五采非水不章。道为功本,功为道效,据功谓之贤,是则道人之不肖也。高祖得天下,赏群臣之功,萧何为赏首。何则?高祖论功,比猎者之纵狗也。狗身获禽,功归於人。群臣手战,其犹狗也;萧何持重,其犹人也。必据成功谓之贤,是则萧何无功。功赏不可以效贤,一也。
夫圣贤之治世也有术,得其术则功成,失其术则事废。譬犹医之治病也,有方,笃剧犹治;无方,才微不愈。夫方犹术,病犹乱,医犹吏,药犹教也。方施而药行,术设而教从,教从而乱止,药行而病愈。治病之医,未必惠於不为医者。然而治国之吏,未必贤於不能治国者,偶得其方,遭晓其术也。治国须术以立功,亦有时当自乱,虽用术,功终不立者;亦有时当自安,虽无术,功犹成者。故夫治国之人,或得时而功成,或失时而无效。术人能因时以立功,不能逆时以致安。良医能治未当死之人命,如命穷寿尽,方用无验矣。故时当乱也,尧、舜用术,不能立功;命当死矣,扁鹊行方,不能愈病。射御巧技,百工之人,皆以法术,然后功成事立,效验可见。观治国,百工之类也;功立,犹事成也。谓有功者贤,是谓百工皆贤人也。赵人吾丘寿王,武帝时待诏,上使从董仲舒受《春秋》,高才,通明於事后为东郡都尉。上以寿王之贤,不置太守。时军发,民骚动,岁恶,盗贼不息。上赐寿王书曰:“子在朕前时,辐凑并至,以为天下少双,海内寡二,至连十余城之势,任四千石之重,而盗贼浮船行功取於库兵,甚不称在前时,何也?”寿王谢言难禁。复召为光禄大夫,常居左右,论事说议,无不是者,才高智深,通明多见。然其为东郡尉,岁恶,盗贼不息,人民骚动,不能禁止。不知寿王不得治东郡之术邪?亡将东郡适当复乱,而寿王之治偶逢其时也?夫以寿王之贤,治东郡不能立功,必以功观贤,则寿王弃而不选也。恐必世多如寿王之类,而论者以无功不察其贤。燕有谷,气寒不生五谷。邹衍吹律致气,既寒更为温,燕以种黍,黍生丰熟,到今名之曰“黍谷”。夫和阴阳,当以道德至诚。然而邹衍吹律,寒更为温,黍谷育生。推此以况诸有成功之类,有若邹衍吹律之法。故得其术也,不肖无不能;失其数也,贤圣有不治。此功不可以效贤,二也。
人之举事,或意至而功不成,事不立而势贯山。荆轲、医夏无且是矣。荆轲入秦之计,本欲劫秦王生致於燕,邂逅不偶,为秦所擒。当荆轲之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医夏无且以药囊提荆轲。既而天下名轲为烈士,秦王赐无且金二百镒。夫为秦所擒,生致之功不立,药囊提刺客,〔无〕益於救主,然犹称赏者,意至势盛也。天下之士不以荆轲功不成,不称其义,秦王不以无且无见效,不赏其志。志善不效成功,义至不谋就事。义有余,效不足,志巨大,而功细小,智者赏之,愚者罚之。必谋功不察志,论阳效不存阴计,是则豫让拔剑斩襄子之衣,不足识也;伍子胥鞭笞平王尸,不足载也;张良椎始皇误中副车,不足记也。三者道地不便,计画不得,有其势而无其功,怀其计而不得为其事,是功不可以效贤,三也。
以孝於父、弟於为兄贤乎?则夫孝弟之人,有父兄者也,父兄不慈,孝弟乃章。舜有瞽瞍,参有曾皙,孝立名成,众人称之。如无父兄,父兄慈良,无章显之效,孝弟之名,无所见矣。忠於君者,亦与此同。龙逢、比干忠著夏、殷,桀、纣恶也。稷、契、皋陶忠暗唐、虞,尧、舜贤也。故萤火之明,掩於日月之光;忠臣之声,蔽於贤君之名。死君之难,出命捐身,与此同。臣遭其时死其难,故立其义而获其名。大贤之涉世也,翔而有集,色斯而举;乱君之患,不累其身;危国之祸,不及其家,安得逢其祸而死其患乎?齐詹问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也,若何?”对曰:“有难不死,出亡不送。”詹曰:“列地而予之,疏爵而贵之,君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可谓忠乎?”对曰:“言而见用,臣奚死焉?谏而见从,终身不亡,臣奚送焉?若言不见用,有难而死,是妄死也;谏而不见从,出亡而送,是诈伪也。故忠臣者能尽善於君,不能与陷於难。”案晏子之对,以求贤於世,死君之难、立忠节者,不应科矣。是故大贤寡可名之节,小贤多可称之行,可得?者小,而可得量者少也。恶至大,?弗能;数至多,升斛弗能。有小少易名之行,又发於衰乱易见之世,故节行显而名声闻也。浮於海者迷於东西,大也。行於沟,咸识舟楫之迹,小也。小而易见,衰乱亦易察。故世不危乱,奇行不见;主不悖惑,忠节不立。鸿卓之义,发於颠沛之朝;清高之行,显於衰乱之世。
以全身免害,不被刑戳,若南容惧白圭者为贤乎?则夫免於害者幸,而命禄吉也,非才智所能禁,推行所能却也。神蛇能断而复属,不能使人弗断。圣贤能困而复通,不能使人弗害。南容能自免於刑戳,公冶以非罪在缧?,伯玉可怀於无道之国,文王拘?里,孔子厄陈、蔡,非行所致之难,掩己而至,则有不得自免之患,累己而滞矣。夫不能自免於患者,犹不能延命於世也。命穷,贤不能自续;时厄,圣不能自免。
以委国去位,弃富贵,就贫贱为贤乎?则夫委国者,有所迫也。若伯夷之徒,昆弟相让以国,耻有分争之名;及大王甫重战其民,?皆委国去位者,道不行而志不得也。如道行志得,亦不去位。故委国去位,皆有以也,谓之为贤,无以者,可谓不肖乎?且有国位者,故得委而去之,无国位者何委?夫割财用及让下受分,有此同实。无财何割?口饥何让?仓廪实,民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让生於有余,争生於不足。人或割财助用,袁将军再与兄子分家财,以为恩义。昆山之下,以玉为石;彭蠡之滨,以鱼食犬豕。使推让之人,财若昆山之玉、彭蠡之鱼,家财再分,不足为也。韩信寄食於南昌亭长,何财之割?颜渊箪食瓢饮,何财之让?管仲分财取多,无廉让之节,贫乏不足,志义废也。
以避世离俗,清身洁行为贤乎?是则委国去位之类也。富贵人情所贪,高官大位人之所欲去之而隐,生不遭遇,志气不得也。长沮、桀溺避世隐居,伯夷、於陵去贵取贱,非其志也。
〔以〕恬无欲,志不在於仕,苟欲全身养性为贤乎?是则老聃之徒也。道人与贤〔者〕殊科者,忧世济民於难。是以孔子栖栖,墨子遑遑。不进与孔、墨合务,而还与黄、老同操,非贤也。
以举义千里,师将朋友无废礼为贤乎?则夫家富财饶,筋力劲强者能堪之。匮乏无以举礼,赢弱不能奔远,不能任也。是故百金之家,境外无绝交;千乘之国,同盟无废赠,财多故也。使谷食如水火,虽贪吝之人,越境而布施矣。故财少则正礼不能举一,有余则妄施能於千,家贫无斗筲之储者,难责以交施矣。举檐千里之人,材?越疆之士,手足胼胝,面目骊黑,无伤感不任之疾,筋力皮革必有与人异者矣。推此以况为君要证之吏,身被疾痛而口无一辞者,亦肌肉骨节坚强之故也。坚强则能隐事而立义,软弱则诬时而毁节。豫让自贼,妻不能识;贯高被?,身无完肉。实体有不与人同者,则其节行有不与人钧者矣。
以经明带徒聚众为贤乎?则夫经明,儒者是也。儒者,学之所为也。儒者学,学,儒矣。传先师之业,习口说以教,无胸中之造,思定然否之论。邮人之过书、门者之传教也,封完书不遗,教审令不误者,则为善矣。〔儒〕者传学,不妄一言,先师古语,到今具存,虽带徒百人以上,位博士、文学,邮人、门者之类也。
以通览古今,秘隐传记无所不记为贤乎?是则〔儒〕者之次也。才高好事,勤学不舍,若专成之苗裔,有世祖遗文,得成其篇业,观览讽诵。若典官文书,若太史公及刘子政之徒,有主领书记之职,则有博览通达之名矣。
以权诈卓谲,能将兵御众为贤乎?是韩信之徒也。战国获其功,称为名将;世平能无所施,还入祸门矣。高鸟死,良弓藏;狡兔得,良犬烹。权诈之臣,高鸟之弓,狡兔之犬也。安平身无宜,则弓藏而犬烹。安平之主,非弃臣而贱士,世所用助上者,非其宜也。向令韩信用权变之才,为若叔孙通之事,安得谋反诛死之祸哉?有功强之权,无守平之智,晓将兵之计,不见已定之义,居平安之时,为反逆之谋,此其所以功灭国绝,不得名为贤也。
〔以〕辩於口,言甘辞巧为贤乎?则夫子贡之徒是也。子贡之辩胜颜渊,孔子序置於下。实才不能高,口辩机利,人决能称之。夫自文帝尚多虎圈啬夫,少上林尉,张释之称周勃、张相如,文帝乃悟。夫辩於口,虎圈啬夫之徒也,难以观贤。
以敏於笔,文墨〔雨〕集为贤乎?夫笔之与口,一实也。口出以为言,笔书以为文。口辩,才未必高;然则笔敏,知未必多也。且笔用何为敏?以敏於官曹事。事之难者莫过於狱,狱疑则有请谳。盖世优者,莫过张汤,张汤文深,在汉之朝,不称为贤。太史公《序累》以汤为酷,酷非贤者之行。鲁林中哭妇,虎食其夫,又食其子,不能去者,山政不苛,吏不暴也。夫酷,苛暴之党也,难以为贤。
以敏於赋颂,为弘丽之文为贤乎?则夫司马长卿、扬子云是也。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锈,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於弥为崇实之化。
以清节自守,不降志辱身为贤乎?是则避世离俗,长沮、桀溺之类也。虽不离俗,节与离世者钧,清其身而不辅其主,守其节而不劳其民。大贤之在世也,时行则行,时止则止,铨可否之宜,以制清浊之行。子贡让而止善,子路受而观德。夫让,廉也;受则贪也。贪有益,廉有损,推行之节,不得常清眇也。伯夷无可,孔子谓之非,操违於圣,难以为贤矣。
或问於孔子曰:“颜渊何人也?”曰:“仁人也,丘不如也。”“子贡何人也?”曰:“辩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客曰:“三子者皆贤於夫子,而为夫子服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辩且诎,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之道,弗为也。”孔子知所设施之矣。有高才洁行,无知明以设施之,则与愚而无操者同一实也。夫如是,皆有非也。无一非者,可以为贤乎?是则乡原之人也。孟子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於流俗,合於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说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孔子曰:‘乡原,德之贼也。’似之而非者,孔子恶之。夫如是,何以知实贤?知贤竟何用?世人之检,苟见才高能茂,有成功见效,则谓之贤。若此甚易,知贤何难!《书》曰:“知人则哲,惟帝难之。”据才高卓异者,则谓之贤耳,何难之有?然而难之,独有难者之故也。
夫虞舜不易知人,而世人自谓能知贤,误也。然则贤者竟不可知乎?曰:易知也。而称难者,不见所以知之则难,圣人不易知也;及见所以知之,中才而察之。譬犹工匠之作器也,晓之则无难,不晓则无易。贤者易知於作器。世无别,故真贤集於俗士之间。俗士以辩惠之能,据官爵之尊,望显盛之宠,遂专为贤之名。贤者还在闾巷之间,贫贱终老,被无验之谤。若此,何时可知乎?然而必欲知之,观善心也。夫贤者,才能未必高也而心明,智力未必多而举是。何以观心?必以言。有善心,则有善言。以言而察行,有善言则有善行矣。言行无非,治家亲戚有伦,治国则尊卑有序。无善心者,白黑不分,善恶同伦,政治错乱,法度失平。故心善,无不善也;心不善,无能善。心善则能辩然否。然否之义定,心善之效明,虽贫贱困穷,功不成而效不立,犹为贤矣。故治不谋功,要所用者是;行不责效,期所为者正。正是审明,则言不须繁,事不须多。故曰:“言不务多,务审所谓。行不务远,务审所由。”言得道理之心,口虽讷不辩,辩在胸臆之内矣。故人欲心辩,不欲口辩。心辩则言丑而不违,口辨则辞好而无成。
孔子称少正卯之恶曰:“言非而博,顺非而泽。”内非而外以才能饬之,众不能见则以为贤。夫内非外饬是,世以为贤,则夫内是外无以自表者,众亦以为不肖矣。是非乱而不治,圣人独知之。人言行多若少正卯之类,贤者独识之。世有是非错缪之言,亦有审误纷乱之事,决错缪之言,定纷乱之事,唯贤圣之人为能任之。圣心明而不暗,贤心理而不乱。用明察非,非无不见;用理铨疑,疑无不定。与世殊指,虽言正是,终不晓见。何则?沉溺俗言之日久,不能自还以从实也。是故正是之言为众所非,离俗之礼为世所讥。管子曰;“君子言堂满堂,言室满室。”怪此之言,何以得满?如正是之言出,堂之人皆有正是之知,然後乃满。如非正是,人之乖刺异,安得为满?夫歌曲妙者,和者则寡;言得实者,然者则鲜。和歌与听言,同一实也。曲妙人不能尽和,言是人不能皆信。鲁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顺祀,畔者五人。贯於俗者,则谓礼为非。晓礼者寡,则知是者希。君子言之,堂室安能满?夫人不谓之满,世则不得见口谈之实语,笔墨之余迹,陈在简?之上,乃可得知。故孔子不王,作《春秋》以明意。案《春秋》虚文业,以知孔子能王之德。孔子,圣人也。有若孔子之业者,虽非孔子之才,斯亦贤者之实验也。夫贤与同轨而殊名,贤可得定,则圣可得论也。问:“周道不弊,孔子不作《春秋》。《春秋》之作,起周道弊也。如周道不弊,孔子不作者,未必无孔子之才,无所起也。夫如是,孔子之作《春秋》,未可以观圣;有若孔子之业者,未可知贤也。曰:周道弊,孔子起而作之,文义褒贬是非,得道理之实,无非僻之误,以故见孔子之贤,实也。夫无言,则察之以文;无文,则察之以言。设孔子不作,犹有遗言,言必有起,犹文之必有为也。观文之是非,不顾作之所起,世间为文者众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论之,可谓得实矣。论文以察实,则君山汉之贤人也。陈平未仕,割肉闾里,分均若一,能为丞相之验也。夫割肉与割文,同一实也。如君山得执汉平,用心与为论不殊指矣。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於《春秋》。然则桓君山〔不相〕,素丞相之迹,存於《新论》者也。
王充论衡?卷二十七?定贤篇翻译
圣人不容易识别,贤人比起圣人来要容易识别些。一般人对贤人尚且不能识别,怎么能识别圣人呢?一般人虽然说能识别贤人,但这话肯定是假的。用什么来识别贤人呢?怎样才能识别贤人呢?
把做官居高位而自身享受富贵的人称为贤人吗?富贵却是由天命所决定的。有富贵命的人,不等于是贤人;有贫贱命的人,不等于是不贤的人。如果一定要以命是否富贵来检验贤还是不贤,那么这等于说决定能不能当官的因素是个人的才能而不是命了。
把君王侍奉得舒心很少有过错的人称为贤人吗?这些不过是阿谀奉承之臣,谄媚逢迎之徒罢了。揣测准君王的心思才说话,寻找到适当的时机才行事,不曾有在朝廷上抵触君王所产生的隔阂,就不会有被贬职和罢官的危险。有的是身体姿态优美,面色漂亮可爱,让君王不憎恶而产生喜爱的心情,对他的恩宠多得超过了限度,这也不能称他是贤人。
把朝廷选拔和举荐官吏时大家都称赞的人称为贤人吗?那么那些经常出头露面为人们所熟知的举荐的人就多,不经常出头露面为人们所不知的举荐的人就少,虞舜就是这样的人。尧曾经寻求贤人,大家就推荐鲧和共工,而由于四岳的制止,致使尧没有得到像舜这样的贤人。由此说来,举荐的人的多少,不能用来作为识别被举荐者贤与不贤的依据。有的人道德高尚而举荐他的人少,有的人才能低下而举荐他的人多。圣明的君王在举荐人的多少之间求善察恶,有时是可以得到善恶的真实情况的。况且广泛结交各种人物,会笼络众心的人,人们喜欢他就称赞他;清廉正直与乡里关系不融洽,志向高洁不结交志向不同之徒,失去了众心的人,人们怨恨他就会毁谤他。所以一个人的好名声多半是由于懂得笼络人心而得来的,坏名声多半是不会讨好众人造成的。
齐威王因为毁谤而封赐即墨大夫,因为称誉而烹杀阿大夫,是因为即墨大夫有政绩而没有受到称赞,阿大夫没有功绩而获得名誉的缘故。子贡问道:“一乡的人都夸奖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还不能肯定。”子贡又问:“一乡的人都讨厌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也还不能肯定。最好是一乡的好人都夸奖他,一乡的坏人都讨厌他。”这样说来,称誉的人多而所有的人都说他好的人,不一定是贤人。好人称赞他,坏人毁谤他,毁谤和称赞的人各占一半,这样的人才可能是贤人。根据好人所称赞的,坏人所毁谤的,就能够识别贤人了吗?如果是这样,孔子的话可以识别贤人,同样不知道称赞这个人的,是不是好人呢?毁谤这个人的,是不是坏人呢?也许称赞这个人的是坏人而毁谤这个人的却是好人呢!人们照样感到迷惑而无法去识别贤人啊。
把众人所归附、宾客很多的人称为贤人吗?而那些众人所归附的,也许是广泛结交各种人物的那种人,众人喜欢他而称赞他,就像蚂蚁聚集一样去归附他。有的处于显贵地位而能给人利益,有的喜好士人而对待宾客谦逊,放下架子以等待贤人的光临。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养了几千个食客,被称为贤君。大将军卫青及霍去病,门下没有养一个宾客,仍然被称为名将。所以宾客的聚集,在于有好士下客的封君,给人以利或害的达官贵人。如果不好士下客,不能给人以利或害,那么众人不归附而士人也不会去归附了。
把居官在位统治人民,得民心受人民歌颂的人称为贤人吗?而这些得民心的人,和那些得士子欢心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用虚伪的恩惠安抚老百姓,老百姓的欲望得到满足,于是就高兴而乐意归附他了。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齐国的田成子和越王勾践就是这样的人。田成子想掌握齐国的政权,用大斗借出,小斗收进而使老百姓喜欢。勾践想洗去被困在会稽山的耻辱,就安抚他的老百姓,慰问死者的亲属和病人而使老百姓高兴。这两个人都各自另有要想达到的目的,而虚伪地引诱招致他们的老百姓,并没有给老百姓以诚心,但老百姓也很高兴。孟尝君半夜要逃出秦关,鸡没有叫关门就不开,一个地位很低的食客用手掌放在嘴边学鸡叫,附近的鸡都应和叫了起来,关门立即打开,孟尝君得以逃出秦关。鸡能够用伪装的声音去感动它,那么人也可以被虚假的恩惠所感动。人可以被虚假的恩惠所感动,那么上天也可以用巧妙的欺诈手段去感动。感动招致天气变化,应当用精诚之心,而人却使用阳燧从天上取到火,用来熔炼五石,在盛夏的五月,浇铸成阳燧,就能取得火。现在又只要把刃、剑和普通的曲刃铜兵器这类东西拿来,向着太阳磨擦,也能从天上取到火。这些刀、剑、钩能从太阳那里取火,那么普通的人,即使不是圣贤,也能够感动天上的气象变化了。就像董仲舒相信用土龙能招来云雨一样,大约也是有他的理由的。如果是这样,应和上天的统治,尚且不能说是贤人,何况仅仅是获得民心,就说他是贤人,怎么样呢?
把任职做官有成就成效显著的人称为贤人吗?用什么来检验任职做官的功绩和成效呢?如果是根据老百姓归附他来检验,然而老百姓是可以用虚假的恩惠来讨好的啊。阴阳之气调和,老百姓安居乐业,是决定于时运。风调雨顺,老百姓安定,即使是不成材的统治者也会碰上太平治世;时运不和,即使是圣王也会遇上乱世。如果根据阴阳之气是否调和来检验贤与不贤,那么尧就会由于洪水成灾而被贬斥,汤就会由于当时的旱灾而被认为统治才能是最下等的了。如果功效指的是具体的事情,那么亲身干这些事的人,功效就会显著可见;运用先王之道来出谋画策的人,功绩就会被埋没而不为人所知。鼓声不合于宫、商、角、徵、羽五音,然而五音没有鼓声配合就不和谐。老师不属于“五服”之亲,然而“五服”之亲没有老师的教导就不懂得互相亲爱。水不属于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然而五种颜色没有水来调和就不鲜明。“道”是具体攻效的根本,具体功效是“道”的表现,根据有具体功效的人称为贤人这条原则,这就是说掌握“道”的人反而被当作不成材的人了。汉高祖得到天下,赏赐群臣的功劳,萧何是受赏赐的群臣中的第一名。为什么呢?汉高祖论功劳的大小,用猎人驱使猎狗来作比喻。猎狗本身捕获了禽兽,功劳却归于猎人。群臣奋力战斗,他们好比是猎狗;萧何沉着稳重,他好比是猎人。一定要根据成绩来称之为贤人,这就是说萧何毫无功绩了。这是根据功效不可以检验贤人的第一点。
圣贤治理国家也有一定的方法,掌握了统治术就功业成就,治理国家不得法事业就要失败。譬如医生治病,有了良方,病情再严重也能治好;没有良方,仅仅是一点轻微的病也治不好。良方就像治理国家的方法,疾病好比国家的祸乱,医生如同官吏,用药好比教化。采用良方药力就发生作用,制定了有效的治国方略教化就会得到推行,教化推行祸乱就会停止,药力发生作用病就会治好。能把病治好的医生不一定比没有把病治好的医生高明。这样说来能把国家治理好的官吏,不一定比不能治理好国家的官吏贤明,只是偶然得到某种方子,碰巧懂得了这种治理的方法而已。治国必须要靠方法来建立功业,也有时运该当国家自身处于混乱之期,即使运用了治国之术,功业始终不能建立的;也有时运该当国家自身处于安定之期,即使没有治国之术,功业仍就能建立的。所以那些治理国家的人,有的正当时运而功业成就,有的背离时运而毫无成就。有治理之术的人能顺应时运而建立功业,但不能够违背时运而使天下安定。良医能医治命不该死的人的命,如果命数已完,寿限已尽,尽管用了良方也不会生效了。所以时运当乱的时候,即使是尧、舜施用任何方法,也不能建立功业;生命该当死亡的时候,即使是扁鹊施用任何药方,也不能治好病。
射箭驾车的技艺,从事各种手工业的人,都运用自身的办法,然后事业取得成功,成效可以明显地见到。治理国家,就像从事各种手工业的人运用办法一样;功业建立,就是事情办成功,如果说做事有功效的人是贤人,这就是说从事各种手工业的人都是贤人了。赵人吾丘寿王,是汉武帝时的待诏,汉武帝派他向董仲舒学习《春秋》,他才干高,通晓事理,后来做了东郡都尉。汉武帝根据寿王很贤明,没有另外向东郡派遣太守。当时由于不断兴兵打仗,老百姓骚动不安,年成也不好,盗贼不断出现。汉武帝赐诏书给寿王说:“你在我跟前的时候,很有谋略,我认为你是天下无双,海内独一无二的人,以至于拥有统辖十几座城的权力,一身担负都尉、太守的重任,而现在盗贼却乘船流动攻占夺取库中的兵器,这和从前你在我身边时的作为很不一样,是什么原因呢?”寿王向武帝谢罪,说骚乱很难禁止。汉武帝又召他为光禄大夫,经常在皇帝的身边,议论任何事理,没有不对的地方。他才能高智谋深,通晓事理而很有见识,然而他做东郡都尉时,年成不好,盗贼不断出现,老百姓骚动不安,他没有办法去禁止。不知是寿王没有掌握治理东郡的方法呢?还是东郡碰巧该当又有祸乱,而寿王去治理恰好又遇上这种时运呢?
凭寿王的贤明,治理东郡却不能建立功绩,一定要以功绩来看是不是贤人,那么寿王就该被贬斥而不该被提拔。恐怕世间必然有很多如寿王这样的人,而评论者却因为他没有功绩就看不出他的贤能。燕国有一个山谷,谷中气候寒冷,庄稼不能生长。邹衍吹奏律管招来暖气,不久之后寒谷变成温谷,燕国用它来种黍,黍长得很好获得了丰收,到今天还称它叫“黍谷”。使阴阳之气调和,应当靠道德至诚之心。然而邹衍吹奏律管之后,寒谷变成温谷,庄稼能够生长成熟。据这种情况来推论各种办得成功的事情,犹如采取邹衍吹奏律管的办法一样。所以掌握了那种方法,即使是不贤的人也没有做不到的事;失去了度数,即使是贤圣,也有治理不好国家的时候。这是根据功效不可以检验贤人的第二点。
人们办事情,有的心意尽到了然而事情却没有办成功,事情没有办成功但是气势却震撼山岳。荆轲和御医夏无且就是这样的人。荆轲到秦国去的计划,原本是想劫持秦王将他活捉到燕国,偶尔不巧,被秦国捉住了。当荆轲追逐秦王,秦王环绕柱子而奔逃的时候,御医夏无且用药囊投掷刺客荆轲。后来,天下的人都称荆轲是壮烈之士,秦王赏赐夏无且二百镒金。荆轲被秦国捉住,没有立下活捉秦王的功劳,夏无且用药囊投掷刺客,对救护君王并没什么好处,然而人们之所以仍然称赞荆轲,秦王仍然赏赐夏无且,是因为他们的心意尽到了气势也很旺盛的缘故。天下的人士不会因为荆轲没有立下功劳而不称赞他的道义,秦王也不会因为夏无且没有做出功效而不赏赐他的心意。心意好就不必检验是否成功,道义尽到了就不必考虑事情是否办好了。道义有余,功效不足,心意巨大而功劳细小,明智的人就会赏赐这样的人,昏庸的人就会惩罚这样的人。如果一定只考虑功效而不考察心意,只论表面效果而不考察内心意图,那么,豫让拔剑砍赵襄子衣服这件事,就不值得记载:伍子胥鞭打楚平王尸体这件事,不值得记载;张良锤击秦始皇误中随从的车子这件事,也不值得记载。三个人都是由于客观环境不利,考虑谋画得不周全,仅仅有气势而没有实际功效,心怀报仇的计划而不能达到报仇的目的。这是功效不可以检验贤人的第三点。
把对父亲孝顺、对兄长尊敬的人称为贤人吗?那些遵循孝悌的人,都是有父兄的人,由于父兄不仁慈,他们的孝悌表现才出名。舜由于有谋害他的父亲瞽瞍,曾参由于有虐待他的父亲曾皙,他们才成就了孝子的名声,众人都称赞他们。如果没有父兄,或者父兄很慈爱善良,便不会有明显的孝悌表现,孝悌的名声,也就不会被发现了。忠于君王的人,也与这种情况相同。关龙逢和比干忠君的名声在夏、殷两代很显著,是由于君王桀、纣很坏;稷、契、皋陶忠君的名声在唐、虞时代不显著,是由于尧、舜很贤明。所以萤火虫的亮光,会被阳光月光所掩盖;忠臣的名声,会被贤明君王的名声所遮蔽。为君王的危难而死,献出生命捐弃身躯,与这种情况相同。臣子遇到国家动乱之时,而死于君王的危难,因此才显出忠君的节义而获得忠臣的美名。大贤人经历世事,像鸟儿那样来回飞翔,察看形势,然后再落下来,受到惊恐就赶快飞走;昏乱的君王所造成的祸难,不会连累到大贤人本身;危害国家的变乱,不会牵连到大贤人的家庭,怎么会遇到那种祸乱而死在那种祸乱中呢?
齐侯问晏子说:“忠臣侍奉他的君王,应该怎样做呢?”晏子回答说:“君王有灾难的时候不为他而死,君王避难逃亡的时候不去护送。”齐侯说:“分地而赏赐给他,封爵位而使他尊贵,君王有难不为君王去死,君王出逃不去护送,可以称为忠臣吗?”晏子回答说:“臣子的建议如果能被君王采用,臣子怎么会死呢?臣子的劝谏如果能被君王听从,君王就一辈子不会出逃,臣下怎么会去护送呢?如果建议不被采用,君王有难时为他而死,这是白白地送死;如果劝谏不被听从,君王出逃时去护送,这是装模作样的行为。所以作忠臣的能尽力给君王提出最好的建议,而不能与君王共同陷于灾难之中。”依照晏子的回答在世间寻求贤人,为君王之难而死,树立忠节的臣子都不符合标准了。所以大贤人很少有值得称道的节操,小贤人有许多可赞美的行为。
能够用?计算的东西是因为它的数目小,能够用升斗量的东西是因为它的数量少。数目非常大,用?就不能计算了;数量非常多,用升和斛就不能量了。稍微有一点特殊名声的行为,又产生在一个衰乱而容易显示节操的时代,所以节操行为显著而名声传遍天下。飘洋过海的人,辨别不清方向,是因为海洋太大了;航行于河沟之中,谁都能辩别船只的行迹,是因为河沟小。河沟小就容易辨认方向,衰乱的时代也容易发现人的节操。所以社会不危乱,奇特的行为就不会被发现;君王不昏庸,忠臣的节义就不会树立。崇高的节操,产生于战乱不安的朝代;清高的品行,显现于衰乱的社会。
把保全自己免遭侵害,不被刑罚杀戮,像南宫适那样被“白圭”诗句所震惊的人称为贤人吗?那些免于受到侵害的人是侥幸,是禄命吉利,并不是靠才智能禁止,靠操行所能避免的。神蛇能使它断开的躯体再连接起来,但却不能让人不斩断它。圣贤能使自己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却不能让人不加害于他。南宫适能自己免于刑戮之难,公治长无辜地被关在监狱中,蘧伯玉在危乱的国家里能深藏自己的政治主张,周文王被拘禁在?里,孔子被围困在陈、蔡之间,这都不是操行不好带来的灾难,灾难突然侵袭自己,就会有自己无法避免的灾难,使自己牵连受害而陷入困境。不能自免于祸患的人,就不能在世间延长寿命。寿命到了尽头,贤人也不能自己使它延长;时运该当受困,圣人也不能自免。
把放弃国家和君王的职位、放弃富贵而归于贫贱的人称为贤人吗?那些放弃国家的人,是因为遭到了某种逼迫。像伯夷这类人,兄弟之间以国相让,可耻有争夺王位的名声,以及太王古公?甫不忍心让他原有的百姓遭受战争的苦难,都放弃国家和放弃王位,是由于道行不通又不得志的缘故。如果道行得通又很得志,也就不放弃王位了。所以放弃国家、王位,都是有一定缘由的,如果因此而称之为贤人,那么没有任何理由放弃国家、王位的君王能称之为不肖吗?况且有国家王位的人,才能够放弃它,没有国家王位的人放弃什么呢?拿出自己的财物让在下位的人得到分给的财物,和这种情况是同一回事。没有财物用什么来分呢?自己都没有吃的又推让什么呢?“粮仓充实,老百姓才知道讲礼节;衣食丰足,老百姓才懂得荣辱。”推让产生于有多余,纷争产生于不富足。有人拿出财物资助别人,袁将军一再把家财分给他哥哥的儿子,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种讲究恩义的行为。昆山之下,把玉当作石头;彭蠡湖边,用鱼来喂狗和猪。假如推让的人,家财像昆山的玉、彭蠡的鱼那样多,家财无论分多少出来,也不值得称赞。韩信在南昌亭长家寄食的时候,有什么财产来分割呢?颜渊家境贫穷之时,有什么财物来推让给别人呢?管仲分取财利时自己多拿,没有廉让的礼节,是由于贫穷不富足,丧失了志气节义。
把远离世俗隐居,身心行为清洁的人称为贤人吗?这就同放弃国家王位的人是一类情况。富贵是人情所贪图的,高官大位是人们乐于想往的,放弃高官富贵而隐居,是由于一生没有受到君王的赏识,自己的报负无法得以实现。长沮、桀溺避开世俗隐居,伯夷、於陵仲子放弃富贵而自取贫贱,这并不是他们的本意。
把清静无为没有欲望,志向不在于做官,只是想保全自身修养情性的人称为贤人吗?这就是老聃这一类人。道家与贤人所以不同类,在于贤人忧伤世道而企图拯救世人脱离苦难,因此孔子日夜忙碌,墨子匆忙不安。不进而与孔子、墨子这样的人从事同样的事业,而倒回去与黄、老那样的人修养同样的品性,这就不是贤人。
把千里赴义,对老师、长官、朋友不废弃礼节的人称为贤人吗?只有那些家财富足,筋力强劲的人才能胜任这种事情。生活贫困就拿不出财物来讲究礼节,体弱多病就不能奔波千里讲究义气,因为他们承受不了。所以拥有百金的富贵人家,就是远在境外也没有断绝交往的;有千乘战车的大国,盟国之间不会废弃相互赠馈的礼节,这是由于财富多的缘故。假如谷物粮食像水火那样容易得到,即使是贪吝的人,也会跨越境界给人们施舍财物。所以财物少就连正常的礼节也不能讲究一点,财富有余就能胡乱施舍给上千的人,家境穷得没有一筲粮食储蓄的人,就难以用交往和布施来责备他了。挑着担子千里奔波的人,执鞭骑马跨越疆界的人,手脚磨出了硬皮,面孔晒得黝黑,不会患体力不支的疾病,他们的筋力皮肤一定有与常人不同之处。据此推论比照那些为长官作证的官吏,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自身受刑吃苦而不肯供出一字,也是由于他们的肌肉骨节坚强的缘故。骨肉坚强就能掩盖事实树立节义,骨肉软弱就会歪曲事实败坏名节。豫让毁伤自身,连妻子也不认识他了,贯高被拷打,全身没有完整的皮肉。壮实的身体与众人有不同之处的人,他的气节操行就有与众人不相同的地方。
把精通经书带学生聚集门徒讲学的人称为贤人吗?那些精通经学的,是儒者。儒者,是靠学习经书才成儒者的。儒者靠的是勤学经书,勤学经书,也就成为儒者了。传授前辈老师的学问,把老师讲的东西背诵下来再用它去教育学生,心中没有一点创见,也不能思考判断论点的正确与否。投送文书的差役递送文书,就同守门人传达长官的命令一样,封记完整文书没有遗失,传达命令清楚转达指示没有错误的人,就是很好的了。儒者传授学问,不随便改动一字,前代老师的古话,至今全部详尽地保存下来,即使带领门徒百人以上,在博士、文学之列,不过是邮人、门者这类人罢了。
把博览古今图书,秘隐传记无所不熟记的人称为贤人吗?这不过是与儒者同类的人。才智高对事物有广泛兴趣,勤奋学习而不间断,就像容成的后代,有祖上留下来的著作,得以继承祖上的书籍,细心阅览认真诵读。或者掌管图书档案,就像太史公和刘子政这类人,有主管书籍文献的职位,也就有了博览群书学问通达的名声。
把权术诈谋奇异,能率领士兵统率众将的人称为贤人吗?这是韩信这类人。国家战乱时建立功勋,称为名将;在社会安定时才能没有地方施展,反倒陷入灾祸之中了。“高飞的鸟被射死,良弓就被收藏起来了;狡兔被猎获,优良的猎犬就被煮了。”有权术诈谋的大臣,就像射飞鸟的良弓、获狡兔的良犬一样。安定和平的时期,这种人没有用处,就像良弓被收藏良犬被烹煮一样。安定和平时期的君王,并不是要抛弃有权术的大臣,轻视有战功的将士,而是他们生平用来辅助君王的本领,已经完全不适用了。假如当初韩信运用善于权变的才能,做出像叔孙通那样的事业来,怎么会有因谋反而被殊死的灾祸呢?具有攻打强敌的权谋,没有安守和平的智慧,懂得领兵的计谋,却看不到天下已经稳定的大势,处在和平安定的时期,却搞叛逆的密谋,这就是他之所以功劳、封国被取消,不能称为贤人的道理。
把有口才而善辩,言语动听言辞巧妙的人称为贤人吗?那就是子贡这类人。子贡的口才超过颜渊,孔子却把他排在颜渊之下。真实的才能并不高,口才机智锋利的人,人们必定会称赞他。自汉文帝赞赏虎圈啬夫,斥责上林尉以后,张释之举周勃、张相如为例,汉文帝因此才醒悟。那些以口才善辩的人,就如虎圈啬夫这类人一样,很难用他们来观察一个人是不是贤人。
把文思敏捷,落笔快得像雨点洒下的人称为贤人吗?笔头快与口才好,实际上是一回事。口说出来就是言语,笔写出来就是文章。口头善辩的人,不一定才高;这样说来,下笔敏捷的人,也不一定多智了。而且文章写得快是应用在什么地方呢?是应用在对官府的事务处理得快吗?官府的事务最难办的莫过于审理案件,审理案件有疑难就用“请谳”的办法。举世善于断案的莫过于张汤,张汤援用法律条文苛刻,在汉朝,并不称他为贤人。太史公排列人物高下,认为张汤是酷吏,残酷并不是贤人的行为。鲁国树林中痛哭的妇人,老虎吃了她的丈夫,又吃了她的儿子,她所以不愿离开那里,是因为爱那里赋税不苛繁,官吏不残暴。酷吏,是苛刻残暴的那类人,很难以他们为贤人。
把善于作赋、颂,能写宏伟华丽文章的人称为贤人吗?那么司马长卿、扬子云就是这样的人。文章华丽而且篇幅巨大,言辞精妙而且旨趣高深,然而文章却不能判断确定是非,分别不出正确与错误的真实情况。即使文章像锦绣那样美,含意像黄河、汉水那样深,老百姓却不能从中明白是与非的界限,这对于制止弄虚作假,崇尚实际教化没有一点好处。
把自守清白的节操,不降低志气,不屈辱身分的人称为贤人吗?这就是远离世俗隐居,长沮、桀溺一类的人。即使不远离世俗,节操却与远离世俗隐居的人一样,保持自身的清白而不辅助君王,坚守节操而不关怀老百姓。大贤人生活在世上,时势适宜做官就出来做官,时势适宜隐居就去官隐居,权衡时势是否适宜,以此来确定操行的清浊以便选择。子贡让财却阻止了别人行善,子路受财却勉励了别人讲道德。推让是廉洁;受财就是贪婪了。贪财而有益于人,廉洁却有损于人,推让与受财的节操,并不可能常常是清高的。伯夷不愿出来做官,孔子反对他的做法。操行与圣人违背,很难以他们为贤人。
有人问孔子说:“颜渊是什么样的人呢?”孔子说:“他是个仁人,我不如他。”又问:“子贡是什么样的人呢?”孔子说:“他是个有口才的人,我不如他。”又问:“子路是什么样的人呢?”孔子说:“他是个勇敢的人,我不如他。”客人说:“颜渊、子贡、子路三个人都比你贤能,而愿为你奔走效劳,是什么原因呢?”孔子说:“我既能仁爱又能残酷无情,既善辩又能言语迟钝,既能勇敢又能胆怯。用他们三个人的能耐和我的这套本领交换,我是不干的。”孔子是知道随机应变去处理问题的。有很高的才能和廉洁的品行,但缺乏明智以随机应变地处理问题,那就和愚昧而无操行的人是一个样了。
如此说来,人人都有缺点。没有一点缺点的人可以称为贤人吗?这就是乡原那种人。孟子说:“乡原这种人,要想指责他,又举不出什么大过错;要想讥剌他,却又无可讥剌。他总是迎合流俗,讨好污世,平日为人好像忠厚老实,行动也好像正直清白,大家都喜欢他,他自己也觉得很不错,但实际上和尧舜之道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孔子说:“乡原是破坏道德的人,”似乎很有德行实际上却并非如此的人,孔子很厌恶他。
如此说来,怎样识别真正的贤人呢?识别贤人究竟根据什么呢?世人的考察标准是,如果见他才高多能,有取得成功的功效,就认为他是贤人。像这样就太容易了,识别贤人有什么困难呢?《尚书》说:“能识别人的就是明智的人,这一点连舜也感到很困难。”根据才能高超杰出的人就被称为贤人来看,识别贤人还有什么困难呢?但是《尚书》既然说难,自有认为难的理由。连虞舜也不容易识别贤人,而世人自认为能识别贤人,就错了。
这样说来贤人就不可识别吗?我说:很容易识别。之所以说它难,不了解用什么来识别贤人就难,即使是圣人也不容易识别贤人。等到知道了用什么来识别贤人,就是具有中等才智的人也可以看出贤人了。譬如工匠制造器物,掌握了制作方法就不难,不掌握方法就不容易制造了。识别贤人比工匠制造器物还容易,世人没有区别的能力,所以真正的贤人混杂在俗士之中,俗士凭能言善辩的小聪明,占据官爵的尊位,期望显耀的荣誉,于是就专断了称为贤人的名声。贤人退居在闾巷之间,贫贱到老死,还要蒙受不见功效的毁谤。
如此说来,到什么时候才能识别贤人呢?如果一定要想识别贤人,就看他有没有善心。贤人,不一定才高但能明辨是非,不一定多智但行止没有错误。用什么来看是否有善心呢?必须根据他的言论。有善心,就有好的言论。根据他的言论而考察他的行为,有好的言论就有好的行为了。言论行为没有错,治家可使亲属之间讲伦理,治国能使尊卑上下有次序。没有善心的人,黑白不分,视善恶为同类,会使政治错乱,法度失去公平。所以只要心善,就没有什么是不好的;心不善,就没有什么是好的。心善就能辨明是非。是非的道理能够确定,心善的功效也就显明了,即使贫穷低微,境遇艰难,功名不成,业绩不立,但他们仍然是贤人。
所以治国不一定考虑功绩,关键在于所依据的道理是否正确;行为不要求功效,那要看所做的事是否纯正。做事纯正、道理正确果真显明,那么言语不必繁琐,事情也不必很多。所以说:“说话不必追求长篇大论,应当努力使所说的话在理;做事不必好高骛远,应当力求所做的事符合原则。”说话深得道理的核心,口才即使迟钝而不善辩说,而善辩已在心胸之中了。所以人追求的是心辩,而不应该追求口辩。心辩就是言辞虽不华美动听,却不会违背正道,口辩就是言辞华丽却没有什么用处。
孔子列举少正卯的罪恶说:“言论错误却显得很博学,附和错误的东西却又加以润饰。”内心歹毒而外表却用才能将它粉饰起来,众人不能发现,就认为他是贤人。内心歹毒而外表却掩饰得很好,世人认为他是贤人,那么内心善良外表却无法自我表露的人,众人也就认为他是不肖之辈了。是非混乱而不治理,唯独圣人能识别是非。人的言行大多如少正卯这类人,唯独贤圣能识别他们。世间有是非颠倒的言语,也有正确与错误混淆不清的事情。判明颠倒的言语,判断混淆不清的事情。只有贤良圣明的人才能够胜任。圣人的心清明而不昏暗,贤人的心有条理而不紊乱。用清明考察谬误,没有什么看不明的;用条理解释疑惑,疑惑没有不能断定的。
如果和世人的意见不同,即使话说得很正确,众人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呢?沉溺在俗言之中日子久了,就不能自拔而服从正确的言论。所以正确的言论被众人所反对,违背世俗标准的礼节被众人所指责。《管子》说:“君子在堂上说话能符合满堂人的心意,在室内说话能符合全室人的心意。”很奇怪这样的说话,怎么能让所有的人都满意呢?如果正确的话说出来,全堂的人都有正确的理解,然后所有的人才会满意。如果在座的人没有正确的理解,人说的话违理怪异,怎么能使人人都满意呢?歌曲很绝妙,能附和的人就很少;说的话符合实际,同意的人也很少。和歌和听话,是同一回事。歌曲绝妙人们就不能都附和,言论正确人们就不能都相信。“鲁文公违反祭祖的正常顺序,有三个大臣离开祖庙;鲁定公按照礼法祭祀,却有五个大臣离开祖庙。”习惯于世俗的人,就说按照礼法做是错的。通晓礼法的人少,那么识别正确与否的人就稀少。君子说的话,堂室中的人怎么能都满意呢?
人不可能对别人说的话都满意,那么世人也就不可能知道别人所说的真实内容,要笔墨写出的痕迹,排列在简策上面,才能得知。所以孔子没有当上君王,就写作《春秋》以表明政治主张。考察《春秋》所阐明的没能得以实行的政治主张,就可以知道孔子具有当君王的品德。孔子是圣人,如果有像孔子那样业绩的人,即使不具备孔子那样的才能,这也是贤人的实际证明。贤人与圣人所遵循的道相同只是名称不一样,贤人既可以确定,那么圣人也就可以论定了。
问:“周代的礼制不败坏,孔子就不会编写《春秋》。《春秋》的写作,起因于周代礼制的败坏。如果周道不败坏,孔子不编写《春秋》,未必他不具备作为孔子的才能,只是没有理由来促使他从事编写。如果是这样,单从孔子编写《春秋》这件事,不能够看出他是圣人;如果有像孔子那样业绩的人,还不能识别他是贤人吗?”
回答说:周代礼制败坏,孔子起而编写《春秋》,《春秋》的文义褒贬是非,深得道理的真实内涵,没有违背礼义不合正道的错误,所以据此可以看到孔子的贤明,是很实际的。没有言论就以文章来考察,没有文章就以言论来考察。假设孔子不编写《春秋》,也还有别的遗留下来的言论,发表言论必定有原由,如同写文章必定有目的一样。考查文章的好坏,而不考虑写作的起因动机,世间写文章的人多得很,是与非不分,对与错不定,桓君山对此的评论,可以说是掌握了它们的实质。依据文章来考察真实情况,桓君山就是汉代的贤人。陈平没有做官时,在乡里分祭肉,每份肉分得完全一样,这是他能当丞相的证明。分肉与评论文章,实质上是一回事。如果桓君山得以掌握汉朝治国的大权,他的用心与论文意旨不会不同。孔子没有当上君王,素王的业绩反映在《春秋》上。这样说来,那么桓君山没有当上丞相,素丞相的功绩已留存在他的《新论》之中了。
【王充论衡 论衡全文 论衡翻译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http://www.jiyifa.net/shiju/518371.html
相关阅读:酒杯_诗歌鉴赏
书生事业真堪笑,忍冻孤吟笔退尖
宋祁《锦缠道?春游》原文翻译及赏析
克鲁伦河_诗歌鉴赏
张九龄《和姚令公哭李尚书?》原文及翻译 赏析